按:2018年4月28日,OCAT研究中心邀请了北京画院副院长、美术馆馆长吴洪亮先生和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吕新雨教授,以“20世纪少数民族题材艺术实践与现代中国建构”为题做了讨论。两位学者从自身的研究领域和实践出发,讲述了20世纪少数民族和地区与艺术创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及其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和政治环境下所呈现的复杂的艺术现象背后不同的成因和意义。本文为吴洪亮先生讲述部分,文字经主讲人修订。
我在研究之初自身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这事值得研究吗?因为20世纪中国美术这个课题本身就一直被学界质疑。在苏立文先生所著的《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中文版序言的开篇部分,他这样写道:“1959年,当我出版西方语言中的第一部研究此课题的专著时,西方同行们批评我为一个不值得严肃对待的课题浪费时间。”其中的原因有两点:没有新东西和模仿西方。很多批评者认为这一时期传统书画没有新意,其他创作形式又基本都是在模仿西方艺术。
对20世纪中国美术的研究与展览,在近年成为新的热点。研究与历史的发展一样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国内外众多美术馆都曾举办过近现代艺术家的个展,如亚洲艺术博物馆2014年举办了齐白石纪念展,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收藏有众多二十世纪的艺术品,等等。因此可以看到这一板块的研究在今天已经不是一个人或者一小部分人在奋斗的事情,而是一个集团性的工作状态。但今日对20世纪中国艺术的研究恐怕还处于资料整理与举证的阶段,无需急于进行全方位的价值判断。
展览是研究的原因,同时也是结果。
一,对实在、可读、具有形象感的背景材料倍加重视;
二,对同一题材作品的图像对照更为视觉化,便于理解;
三,让历史在同一空间与时间再次相遇,如同重新排演的一出戏剧,别有意趣。
总之,以展览的形式呈现美术史的研究成果,是将美术史形象化的过程、活化的过程、传播的过程。
在国内,对于20世纪中国美术的研究曾是件尴尬的事情,我个人感到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因变迁而遮蔽;其二,因太近而不够清晰。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很多消失了或被湮没的东西还没有被真正全方位发掘。此外,许多依旧健在的二十世纪的艺术家,其口述的历史的真实性还需再考证,里面存有太多的态度和自我。但无论是史学研究还是策划展览,这都是一个需要做功课的事情。
写生是艺术创作时重要的手段,同时也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态度。20世纪对于“写生”这一方式无疑是幸运的,无论是社会的需求,还是艺术生态的需求,都要求中国的艺术从天要回到地,开始重新关怀此时此刻的世界以及人本身。
写生是艺术家运用眼、手与世界搭建的一座最为直接的桥梁。20世纪前期主张的写生是为了摆脱徐悲鸿所痛斥的那些中国传统艺术的积习,为了进入一种将艺术“科学化”、“现实化”、“服务化”的需求,因此需要通过到生活中的写生带给中国艺术新的动力。
1920年代至1930年代前期的中国,虽依旧处于动荡之中,但整体的社会发展是进入20世纪以来最为迅速的一个时期。甚至有把1927年到1937年称为“黃金十年”的说法。1931年至1936年间,中国工业成长率平均高达9.3%。在经济发展良好态势的背景下,学术上的思考与争鸣也异常活跃。
对于“真”的追寻,除了源于“西学东渐”借鉴西方艺术的创作方式之外,也与 “社会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引入中国有关。这种以所谓“科学”为基础的了解国家各民族、各地区风土人情,吸收更广泛营养的方式,成为了一时的风气。
这里不只是美术,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诸多学者如周作人、顾颉刚、常惠、董作宾等都开始关注民间文艺学的研究。音乐方面则有赵元任对于民间音乐的开创性探索。梁思成所建构的“营造学社”更以“田野考察”的方式对中国古代建筑进行实地研究。这样的学术背景成为一大批学者、艺术家到西部地区以及民间艺术进行考察的理论的支撑。
推出的“庞薰琹、吴作人、孙宗慰、关山月20世纪30、40年代的写生及其创作”的展览,则是对四位艺术家及其作品进行专题性、断代式的比较,应该说是一次对具体艺术家个案进行交叉、比较与延伸的研究性展览项目。
庞薰琹、吴作人、孙宗慰、关山月这四位与西部结缘的艺术家应该说是20世纪中国艺坛在不同角度颇具代表性的艺术家。庞薰琹涉足广泛,绘画、广告、设计、装饰史研究等多方面,更重要的他是中国工艺美术及教育体系的奠基人。吴作人与孙宗慰同出自徐悲鸿门下,吴作人不仅在艺术上领一代风气,应该说更是徐悲鸿艺术体系最重要的继承者与推进者。孙宗慰则在绘画之外成为中国戏剧舞美基础教学体系的奠基人之一。关山月可谓是“岭南画派”二高一陈之后的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到边疆的写生与创作,不是偶然的孤例,而是一个时代内外因发酵的结果。这一行为是艺术家自发的、主动的与那片土地的一次更为纯真的接触。此次展览则是对这四位艺术家的断代研究,所以对他们之间的许多因缘关系,恐怕首先要梳理一下。
庞薰琹、吴作人、孙宗慰都是江苏人,庞薰琹与孙宗慰甚至是同乡,孙宗慰与关山月同是中华民国元年出生。庞薰琹与吴作人两位都留学欧陆,另两位则在本土完成了美术教育。40年代前后,他们先后到达西部,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位艺术家赴西南、西北的写生与创作成为他们高峰期到来的起点。他们都去过敦煌,对其艺术的临摹、研究与理解成为其人生的重要节点。
1939年,庞薰琹前往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就是因为当时中央博物院下达的考察任务,开始了他对西南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艺术资料的收集与研究的工作。在客观上,他从艺术的角度,凭借其艺术家的独特眼光收集了大量资料,并深入到贵州少数民族的山寨,亲身体验婚礼、丧葬等活动之中并进行了详尽的记录与分析。以此为基础,庞薰琹创作出一批反映西南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构成了他由法国留学归来后创作的一个高峰。
孙宗慰的西北之行源于1925年张大千对敦煌产生了极大兴趣,他希望以一己之力前往敦煌考察、研究。1941年,孙宗慰在吕斯百的举荐下作为张大千的助手从重庆出发,踏上了西行之路。在敦煌孙宗慰帮助张大千进行了摹绘壁画、为洞窟编号等工作。在此行往返的路途中,孙宗慰对西北地区的民风地貌有了最为直观的了解与感悟。因此,这一临摹、考察活动成为他艺术创作的分水岭。
使艺术家们在这一时期不约而同地进入西部还有一个原因,正是由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使大批高等院校的教师、众多学者汇聚到四川、云南等地,边远地区成为远离战争的治学之所。“在战争中逃亡滞留在内地的艺术家,他们在大西北、西南边陲和西藏发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因此,事物的两面性充分地体现出来,学者、艺术家对于西部的研究与描绘成为天时、地利、人和的状态。
庞薰琹、吴作人、孙宗慰、关山月四位的边疆之缘,恐怕要感谢前文提到的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那一年,庞薰琹与齐白石、溥心畲、黄宾虹、王临乙、常书鸿等人同在国立北平艺专教书。由于战争形式紧迫,北平艺专南撤。1938年,与杭州艺专于湘西沅陵合并,改名为国立艺专。1939年秋,由梁思成、梁思永介绍,庞薰琹进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工作。11月初,他开始在博物院从事西南少数民族艺术传统的研究。如前文所说,他承担了赴贵阳、花溪、龙里、贵定、安顺等八十多个苗族、仲家族村寨调查的任务 ,收集当地的服饰、工艺、民谣民歌等民俗资料。这也激发了他在1941年的创作。
吴作人于1935年回国,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讲师,那时孙宗慰是在校的学生。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大学迁往重庆。1938年,吴作人组织“中央大学艺术系战地写生团”开赴第五战区,在潢川、商丘等地画了大量速写,宣传抗战,孙宗慰是成员之一。1941年,如前文提到在吕斯百的推荐下,孙宗慰作为张大千的助手前往敦煌,更对沿途的少数民族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绘制了一大批该题材的作品。
1942年9月孙宗慰回到重庆,就职于中国美术学院。孙宗慰根据所见所闻及收集的资料完成的油画《蒙藏人民歌舞图》更成为他一生中的重要作品。
1943年,吴作人到达成都。此后,吴作人踏上了西北之行的征途,远赴兰州、西宁、敦煌写生、临摹壁画。几乎同期,关山月在重庆举办“西北风景写生画展”后,偕妻子李秋璜和赵望云、张振铎同行,沿河西走廊奔赴敦煌。或许是由于机缘,吴作人与关山月在兰州相遇了,两人甚至骑在骆驼上互画了一张“小像”。关山月题“卅二年冬与作人兄骑明驼互画留念时同客兰州 弟关山月”。吴作人题:“卅二年,山月兄骑明驼互画留念作人”。
我想说的是在去西部以后,大家其实看到的东西可能是相似的、是一样的,可是每个艺术家画的是不一样的。
关山月的创作有一个特点,他说自己如果不出去、不行走,不去写生、就不会画,这是他一辈子的特点。关山月一直是对象反射给他的信息,他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自我的笔墨和程式的生成,他可以根据对象来改的。
这是他画的一幅人物画,大家看这个裙子,静态的是这样,如果动态的时候它就变成了摹古。他很会用自己手头的一些笔墨游戏来画。
我们对比一下关山月、庞薰琹两个人画的同一样的东西。左边是关山月,右边是庞薰琹。面对同样的一个形象状态的时候用的笔法是不同的,两个人的心态也是不一样的。关山月其实还是更多的速写性的描摹,就是我们去看哪怕庞薰琹的速写都不会用这样的一个笔墨关系去画,而且庞薰琹更多的是西画逻辑,虽然他生活在一个中国文人气氛,或者说江浙气氛浓的地方。
其实你会看到,虽然岭南这一派受西画的影响很深,但是从“二居”开始还是保有这些笔墨关系,它是用写意的或者用笔墨直接给它提出来。而庞薰琹的白描其实它已经有很多西画的因素了。比如说帽子这条线和裙子这条线,你可以对比《八十七神仙卷》,绝不是这么画的,这一看就有西方的空间逻辑了,他其实已经试图在他的白描线里头加入理解的那个透视逻辑的空间线。
我们看1949年初孙宗慰画的《蒙藏人民歌舞图》。他在西部得到了一些不一样的综合修养,它跟徐悲鸿的写实教学系统已经拉开了很大的距离,然而1949年以后他又画回来了。它这里头不仅仅有徐悲鸿法派的东西,还有当时的前苏联马克西莫夫带来的苏派的东西,因为那时候只有画这样的才能得到一些认可。后来去了中央戏剧学院,他跟冯法祀老师一块给中央戏剧学院建构了到今天还在延续的舞台美术专业的基础教学的体系,然后他们做了一些很好玩的实验,就是叫做戏装写生,直到今天中央戏剧学院还保存着这一方式。
这四位艺术家从1930年代至1940年代前后赴西南、西北写生、创作、展览以及他们之间的交往的情况大致做了叙述,从中提供的信息有几点值得注意:一,西部提供给他们新鲜的视野,激发了创作新面貌的形成;二,西部成为他们之间交往的重要纽带;三,这批作品成为其一生中的重要作品,随后的展览、出版也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关注。
1949年之后,庞薰琹、吴作人、孙宗慰成为中央美术学院的同事。1957年之后,由于政治等原因,庞薰琹和孙宗慰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吴作人与关山月虽也历经磨难,但一直属于被光环所笼罩的艺术家。这样事实的产生与历史有关,与他们个人有关,而产生的起点则源自他们选择的艺术道路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而西行是产生这一结果的最早预兆。
我们现在谈论他们年轻时期在西部的事情,每个人都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年老后变得平和,而这平和的背后有一点令人伤感。回望20世纪是中国艺术原有独特性日渐模糊的过程,也是新的独特性在逐步形成的过程。上世纪30、40年代到西部的写生与创作是将单纯的形式主义追求与技法的诉求,拉回到与现实世界相关的艺术范畴中进行思考与表达的过程。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为展览前期资料整理做功课,这一时期的美术都有很多值得再思考、再评价的的事情。
作者:吴洪亮,来源:OCAT研究中心
关键字:写生,徐悲鸿,艺术家,敦煌,展览,世纪,艺术,艺术观点争鸣内容标签: 写生 徐悲鸿 艺术家 敦煌 展览 世纪 艺术 艺术观点争鸣


献给世界,你的真心,以致来世,以致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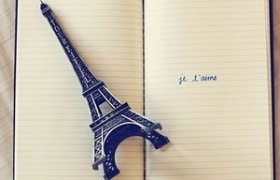
新国学理论
新国学2021年元旦新年贺词
明学与明品生活
文化革命、人类物种与理想社会和人生(一)引言
中医之数理科学化改革与基元系统人体数理模型
新国学的目标及启蒙运动
人性之声HK--悲惨世界
人性与是非善恶
关于美与艺术的内在原理之摘抄
理想的社会
宗教裁判法
对义务教育的批判
社会仿生的原理
新国学的精神
史书重修的一个原则
重修虚幻愚民的历史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