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某个人,走过来,说出这样的话语:“我对绘画中的习语感兴趣。”
你得到了这幅画作:在话音的绵延中,说话者面无表情,一动不动,谨小慎微,而不做出任何动作。也许,在你所期待之处,在脑袋附近,围绕着比如“在绘画中”这么一些词语,他并没有摹仿引号的两个尖角,没有用手指在空中比划,描摹一种文字形式。他只是走过来,向你宣布:“我对绘画中的习语感兴趣”。
他走过来,他刚刚走过来(vient de venir),框架却正在消逝,一切语境的边沿都敞开了,广阔无垠。你也并不完全处在黑暗中,但他到底是想说什么呢?
他是说,他对“绘画中”的习语感兴趣吗?他是说,仅仅对“绘画中”的习语本身感兴趣吗?“绘画中的习语”,本身就是一个强烈习语性的表达,但何为一个习语呢?
或者是说,他对这个习语性的表达本身,对“绘画中”的词语感兴趣?还是对绘画中的词语,对“绘画中”的词语感兴趣?还是对“绘画”的词语感兴趣?
或者是说,他对绘画中的习语,即属于习语的东西,习语性特征或风格,即绘画领域或其他领域独异之物、专属之物、不可摹仿之物感兴趣?或者用另外一种可能的翻译,对图画艺术、绘画必须成就的那种“语言”的独一无二性和不可还原的特殊性感兴趣?如此等等。
如果你善于数计,至少有四个假设,但每个假设都再次分化,而其构成要素被嫁接到其他所有的假设,并彼此污染;那么,你绝对不能完成它们之间的互相转译。
我也不能完成。
如果你花时间在几页书上停留片刻,你就会发现,我主宰不了这种情境,或者说,无法移译也无法描述这种情境。我不能报道正发生于这种情境之中的事态,不能叙述、不能描述、不能宣告、不能摹拟这样的事态,不能提供给人来阅读,不能不留残余地将之形式化。我总是必须将这种特有的、我总是在努力减轻的不确定性予以更新、加以复制,以及再次将之引入到我的传奇之形式化秩序之中——而我的传奇每一次都超重地负荷着某些补充物。在这条路线的尽头,恰恰好像我方才所说:“我对绘画中的习语感兴趣。”
如果我现在写它几回,让这文本负载引号,负载没有引号的引号,负载斜体字,负载方括号,负载图画的形式(姿势),甚至当我按照一切规则而多次使用精致的标点,那么我就敢于打赌说,最初的剩余物最后都会回归。它可能已经开启了一种分离的源始驱动力(a divided Prime Mover)。
我现在让你和一些人在一起,他们走过来且说:“我对绘画中的习语感兴趣”。但这个人,绝对不是我。
二
《绘画中的真理》有塞尚的签名。这是塞尚的一个说法。
它回响在本书的标题之中,听起来就像是一笔债务。
于是,将它归还给塞尚。首先,将他归还给比我早些就引用过的达米施,[1]我们要承认这是一笔债务。我们必须清偿这笔债务。以便这笔欠款(trait)能归还给其合法的主人。
但是,绘画中的真理永远是某种亏欠之物。
塞尚许诺,他要偿还这笔债务:“我欠你绘画中的真理,我将说与你听。”(塞尚1905年10月23日至艾米丽·伯纳德的信)
一个奇特的表达(说法)。说话者是名画家,他在说,而不是写,因为这是一封信,这句“隽言妙语”写下来比说出来要容易得多。他在写,用一种什么也不呈现的语言。他没有让什么被看见,什么也没有描述,而且再现更少。这个句子绝然不以陈述/断言(constative)的方式起作用,
存在于它所构成的事件之外,而是以一种被言语行为理论家称之为“述行语句”的表达,或者更准确地说,以一种所谓“许诺”的述行语句,完成了签名行为。此时此刻,我从言语行为理论家那里仅仅是借取了某些方便的近似表达式,真正说来它们只是某些难题的名称,而确实不知道是否真的有纯粹“记述语句”(constatives)和“述行语句”(performatives)这么一些事情。
塞尚做了什么?他写他能说的,但用了一个没有断言的说法。这个“我欠你”可能涉及到一个描述性指称(我说、我知、我理解“我欠你”)。但它本身却又联系于一种对债务的认可——在它描述之时,它也亏欠:它认可。
塞尚的许诺,一个以其签名联系于绘画史某种事件的人所做出的,且同其身后不止一人相联系的许诺,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许诺。他的行为在表面上并非许诺以记述的方式言说,而是再次许诺“去做”。这个行为许诺了另一个“述行语句”,其许诺的内容如其形式,取决于这另一个述行语句。述行之增补性因此而趋向于无穷。没有任何描述性或记述性指称对象,这个许诺制造了一个事件(它以表述行为“做点什么”),其条件则是:某种约定俗成的架构行为,换句话说,一种述行式虚构所界定的语境,确保了这个事件的可能性。从今以后,这个许诺就没有像“言语行为”那样制造一个事件:作为一种对于存在或构造行为的增补,它“产生”了一个仰赖言语述行结构的独异事件——产生了一个“许诺”。可是,经由另一次增补,这个许诺的对象,以许诺作出的许诺,乃是另一个述行语句,一种“说法”——它可能也是(不过我们尚不知道)一幅“画作”——这幅画既没有说什么,也没有描述什么,如此等等。
依据经典的言语行为理论家们说的看法,完全实现这么一个事件的条件之一,解开事件链条的条件之一,可能是塞尚必须想说点什么,而我们也应该可以理解他所说的。而当像艾米丽·伯纳德这样的人开始拆开一封信的时候,这个条件也是虚构的成分,换言之,是一系列约定俗成的源始蓝本之一。
让我们假设,我写这部书,目的就是要查明这么一种条件是否总是能得到满足,在对这个条件做出界定(仍然有待理解)的同时是否存在过某种意识(感觉)?言语行为理论在绘画中有没有对应的理论?它是否了解为画之道?它势必永远求助于意图、真理和诚实的价值,因而一种绝对的源本也一定会对第一个问题犹疑不决:为了亏欠、甚至为了偿还(rendue),真理必须存在吗?真的存在绘画中的真理么?如果说,绘画中的真理乃是由偿还行为构成,那么,当我们许诺将真理本身作为一份债务、作为一个被偿还的总额(un rendu)而偿还的时刻,我们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究竟是什么意思,去偿还?
约束呢?绘画中的约束呢?
让我们拆开这封信,在艾米丽·伯纳德拆信之后。于是我们看到,“绘画中的真理”可能构成了独具一格的塞尚风格。
据说,他签名确认,以此作为智慧机锋之标记。我们如何得以认出这种独一无二的风格特征呢?
首先,我藉以辨认其风格特征者,乃是:仅当风格特征之独异性为了同一种语言的游戏、语言的机缘和语言的体系相连而自我分离之时,这个事件、这个双重不确定的双重事件才得以缩约,且同自身缔结一纸契约。如果真的存在着任何(数量上)纯而又纯的习语方言,那么我们就应该能实实在在地在塞尚的这种特殊笔触之中认出它们。惟有它们才能提供如此经济的形式化表达方式,高度简略地节约自然语言,只要仍然存在一些剩余物,它们都能以如此少的词语言说这么多的事物,进而盈余和溢出完美的椭圆,通过让经济服从偶然,从而让经济继续运转。
让我们假设,为了这种剩余物的利益,为了这种剩余物的恩典,我冒险分四步,撰写这本书。
剩余——不可翻译之物。
我所说的并不是“属于绘画中真理”这个习语,而是指语风之习语(idiom of locution),因为单单靠引号还不足以让我们相信:问题之本质在于绘画中真理的“习语”,在于这种奇特语风似乎可能指称的习语,以及在于可能早就已经按照多种方式来理解的习语。不可翻译:这种语风也绝对如此。如果有足够的时间、空间以及耐性,在另一种语言之中,更绵长的话语也可能提供理解它的方式,十分艰难地接近它。可是,在其万分简约的表现行为之中,在其笔触描绘的椭圆之中,在其简约/缔约(contract)的逐词逐句与一笔一划之中,它仍然是不可翻译的:像许多词语、记号、字母一样,同一语义内涵的同等数量或同等花费,都具有剩余价值的同等利润。这就是我感兴趣的;当我说“我对绘画中真理的习语感兴趣”时,所指的就是“这种利益”。
你可能总是在尝试翻译。
至于意义,至于这种恰到好处的笔触构成了何种意义,我们是否必须用一种再也不可能关注教学代价的翻译来予以解释?至少有四种意义存在,不证自明地(concesso non dato)假设每一个意义的整体仍然是不容破损的。
1.从属于物自身之笔触/特征(a trait)。由于这种强力归属于绘画(直接再现、偿还、对等、透明,等等的强力),用一种不成画境的法语说,“绘画中的真理”可能意味着和可以理解为:私下地被归还的真理本身,没有中介、没有补充、没有面具、没有面纱的真理本身。换言之,真理本身乃是真的真理或真理的真理,以其偿还强力来偿还的真理,看起来充分地像其自身而逃避一切错置、一切幻象、甚至一切再现的真理,或者已经足够地区分而类似、产生或自我催生两次的真理——具有双重属格的真理:真理之真,真之真理。
2.因此,从属于在虚构秩序之中或其肖像的浮雕之中对等的再现。用法语说,如果这么一种真理存在,且不成画境,那么“绘画中的真理”可能意味着和可以理解为:一笔一划而且忠实地再现在其肖像画之中的真理。这就从反映走向了寓言。因此,真理就再也不在以绘画来再现真理的东西之中,真理仅仅是真理的重影,不论这种类像是多么出色,依据类像之理它恰恰就是另类。真理之真理仍然具有双重属格,但这一次对等的价值拒斥了解蔽的价值。真理的绘画在再现真理之时可能对等于它的原模,但在呈现真理之时它却不能显现真理本身。但是,由于这里的原模就是真理,即那种呈现或再现的价值、解蔽或对等的价值。塞尚的笔画敞开了深渊。【在《艺术作品的起源》中,海德格尔提到,“笔画”(Riss)不仅敞开了深渊,而且把深渊对面的两个边沿合在一起。】如果我们正确地理解塞尚的句子,真理(呈现,再现,解蔽,对等)就必须既利用呈现又利用再现、依据真理的两个原模而被偿还在“绘画”之中(必须以“绘画”来偿还)。真理,画家的原模必须依据真理的的两个原模而被偿还在绘画之中(必须以绘画来偿还)。从此,“真理之真理”,这么一个深奥莫测的表达式,将会让它说出“真理不是真理”,而且可能自己将自己钉上十字架,自我删除,其根据是所有的交错配列法则,而取决于我们决定原模是呈现物、还是再现物。再现之呈现,呈现之呈现,再现之再现,呈现之再现。我们正确地数计了它们么?至少,这造就了四种可能性。
3.归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呈现或再现的画境(picturality,绘画性)。真理可能依据另外一些原模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得以呈现或再现。在此,乃是以绘画的方式来呈现或再现的:而且,不是以(通常意义上的)话语、文学、诗歌和戏剧的方式来呈现或再现的;也不是被呈现或被再现在音乐的时间之中或建筑与雕塑的其他空间之内。所以,我们得到了专属艺术之物,专属签名艺术之物,专属画家塞尚的签名艺术之物。专属艺术之物,以及一种真正意义上理解的、可是这一次却是“表达在绘画之中”的艺术。我们不会按照前述两种情形来理解:那里的绘画将一个碰巧是真理的原模之呈现或再现修辞化了。但是,这种转义修辞化对于其他艺术呈现或再现的逻辑一样有效。用法语说,如果有一种一是一、二是二的真理(本质的真理),而真理却不是一幅画,那么“绘画中的真理”可能意味着和可以理解为:以画境的方式或真正的绘画方式,被显现、被呈现和被再现在真正说来的绘画领域之内的真理,即便对于真理本身,这种方式乃是转义修辞。毫无疑问,为了理解“绘画中的真理”这个表达式,我们就必须抛弃一点惯用法的更大力量(它假设有严格的标准来评价这种真理),但仍然信守语法、句法甚至语义规范。但是,这就一条习语之本质,如果真的有习语这种东西的话。它不仅固定了一个“焦点”在经济上的简约得体,而且调节着游戏、弥散、歧义的可能性——准确地说,调节着笔触风格的整体秩序(整体经济)。这种秩序(经济)自我寄生。
4.归属于绘画秩序,且关于绘画主题,而不仅牵连真理的呈现或再现之画境的真理。“绘画之中”这个表达式之主动的自我寄生,才蕴蓄一种新的意义:相关于绘画的真理,即那种所谓“画境”的艺术上的真实之物。如果我们在这种或那种意义上以其真理价值来规定那种艺术,那么我们就该理解“真上之真”。用法语说,如果有一种一是一、二是二的真理,而真理却不是一幅画,如果它仍然可能让其系统自我寄生,那么,“绘画中的真理”可能意味着和可以理解为:绘画领域之内,且关于绘画主题的真理,【它】存在于绘画之中,正如存在于“绘画中可认知的真理”这一说法之中。我欠你关于绘画的真理,我将说与你听,因为绘画应该是真理,所以我欠你关于真理的真理,我将说与你听。作为习语系统的语言系统,在其自由自在的寄生之中,也许寄生于绘画系统,更准确地说,它将通过比喻的方式显露这种本质的寄生过程,让一切系统都朝外部敞开,分割意在标画边沿的线路(笔触)的单一整体。边沿的分隔也许被镌刻和将发生在本书中所有地方(se passe partout);源始草图-源始框架在其中无限增殖,无始无终:从题词(lemmata)到装饰(parergon),从钱币铭文(exergues)到漩涡装饰(cartouches),本书从边框(passe-partout)这个习语开始。我们常常情不自禁地相信这条习语:真正说来,假想它只道说一件事,而且仅当将形式与意义如此严格地联系起来以至于完全能够转译的时候,它才道说这惟一的一件事。可是,如果真的有这条习语,如果它就是它被认为的那样必须存在,那么,它就不会是那样,反而会失去全部力量,不会造就一种语言。它就会被剥夺它赖以产生真理效果的条件。如果说,“绘画中的真理”一语具有“真理”的力量,在其力量的游戏中向着深渊敞开,那么,绘画之中最关键的,就是真理,在真理之中最关键的(那条习语),就是深渊。
塞尚的笔触线描十分轻易地被解放出来,免于一种当下语境的约束。但是,有必要知道这是一名画家的签名所确认的吗?甚至还可以说,它的力量还取决于这种同语境的规定作游戏,而不让自己不确定的能力。毫无疑问,这种线描风格乃是作为一个边框来发生作用。它迅速地流动在种种可能性之间。灵敏得令人困惑,它移置了重音或看不见的标点符号,它让巨大的话语产生了势能,赋予巨大的话语以形式,以及经济地利用了巨大的话语,它增殖了交易与交往、走私与贪污,寄生在它们之间。但它只起一个边框的作用,这仅仅是一种表象:它意味着一切,也意味着虚无。此外,像(在严格意义上)一切边框一样,它必须在形式上、以自己独有的形式服从一个有限的约束系统。
一个边框有什么作用?它导致什么被完成、被显现?
注释:
[1] Hui thèses pour (ou contre?) une sémiologie de la peinture, Macula 2(1977)。“按照塞尚这个故意含糊其辞的说法或表达……。”我从达米施那里取来“说法”一说,但我并非就事论事,取其字面意思,而是仍然总是对蓄意的界限有所保留。
作者:德里达 胡继华 译 ,来源:中华美学学会公众号
关键字:感兴趣,许诺,绘画,再现,真理,画境,呈现,艺术观点争鸣内容标签: 感兴趣 许诺 绘画 再现 真理 画境 呈现 艺术观点争鸣


献给世界,你的真心,以致来世,以致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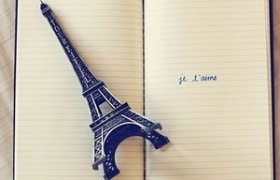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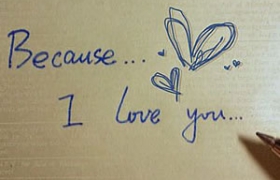
新国学理论
新国学2021年元旦新年贺词
明学与明品生活
文化革命、人类物种与理想社会和人生(一)引言
中医之数理科学化改革与基元系统人体数理模型
新国学的目标及启蒙运动
人性之声HK--悲惨世界
人性与是非善恶
关于美与艺术的内在原理之摘抄
理想的社会
宗教裁判法
对义务教育的批判
社会仿生的原理
新国学的精神
史书重修的一个原则
重修虚幻愚民的历史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