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2002年我成了潘家园的常客。
最早接触潘家园是因为早期卖老北京文玩的华声天桥,我周末基本都泡在里面。老北京对花鸟鱼虫和各种小玩意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20世纪90年代,打记事起我爹就骑自行车带着我混龙潭湖鸟市和潘家园,接触最多的就是核桃、葫芦和橄榄核。那时候老天桥等几个市场都是常摊,只有潘家园周六大早会有外地艺人和作坊来北京批发,我就开始和一些卖不干净东西的摊主打交道,过上早上4点混鬼市捡漏的生活。潘家园的鬼市和老北京传统意义上的鬼市还不太一样,那时候的潘家园周末市场按照时间会有不同的人在卖东西,一般做大宗批发各种作坊手工制作的东西,比如香桶,各种盒子、核雕、菩提子、葫芦、青铜器,卖主都是外地人,夜里进北差不多8点之前人就甩干净货走人了,代替他们的是一些半零售、半批发的商户, 卖的东西也千奇百怪—从古籍善本、信札手记到皇帝诏书,小到弹球大到紫檀顶箱柜,五花八门。有好多是家里老人没了,孩子就把老物件处理了。到中午这些人就走得差不多了。周六下午开始到周日基本上都是固定摊位,批发一些常规的东西。

最有特色的还得是周六早上,有点老北京的古风。我那时候还真没赶上“拉小手”( 古玩行在袖子里商量价格),但是卖挖出来的东西可真不少,而且真能买到老东西。我记得当时买了不少蜻蜓眼(古时琉璃饰物),路分很高,非王侯将相不可,和曾侯乙墓出土的别无二致。不像现在一眼望去全新的,后来总被人问我怎么看这玩意儿的真老,我和他们说,主要原因是你现在没见过真的,没上过手。我在那个时候学会了“望气”,有些时候东西拿不准,看看卖货的人。常年卖坑货的人的气息都是阴沉的,如果你能在大夏天感到一丝凉意,这东西十有八九就错不了。我记得那时候东西又便宜又多,几百块钱就能买到战汉的印纹陶罐。

这个时期我在潘家园认识了大量老北京手艺人。老北京人都知道,旗人多才多艺, 非常有艺术细胞。二三百年前挥着大刀片入关的旗人,二三百年之后他们的后人几乎有一半都是艺术家或者准艺术家,为什么呢?当时对旗人有这样的规定,所有的旗人子女,生下来就是旗人。八旗制度规定,连王爷、亲王、贝勒、郡王、贝子这样一些人,如果没有皇上的批准,都不能出北京城。还规定他们的钱不能办实业,不能做其他生意。他们的时间、精力都没有地方宣泄,只能自娱自乐。从乾隆年间,皇上就给这些旗人发一种叫作龙票的东西。所有手持龙票的人就叫作票友,他们可以组织一个团体叫作票房。票房里面的人可以进行任何的艺术活动,但是不能卖票。于是旗人就把他们大量的精力、才智消耗在文化、艺术上来消遣。旗人在最细小的地方花费了最多的心血。没有票房了之后,潘家园和老天桥就成了这些手艺人的聚集地。

大概一年多没去过如今的潘家园了,因为缺少了之前的乐趣。随着这几年文玩的火爆,这里变成了小商品批发市场。别说捡漏了,恨不得去5家都卖同样的东西,价格也不会有大于20% 的偏差。正经的老东西基本绝迹,老古玩行的规矩也逐渐消退。移动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的兴起,把整个行业拉平了。信息逐渐对等,没有了“捡漏”和“吃药”的大起大落,潘家园也就逐渐丧失了自己的魅力。之前在这里能找到中华民族各个朝代的东西,也见证了中国的兴衰。而潘家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谁能逃过兴衰起伏。是再来一次文艺复兴,还是改朝易代?我们只能远远地观望。
关键字:都是,潘家园,内容标签: 都是 潘家园


献给世界,你的真心,以致来世,以致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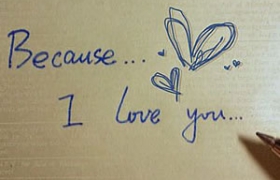



新国学理论
新国学2021年元旦新年贺词
明学与明品生活
文化革命、人类物种与理想社会和人生(一)引言
中医之数理科学化改革与基元系统人体数理模型
新国学的目标及启蒙运动
人性之声HK--悲惨世界
人性与是非善恶
关于美与艺术的内在原理之摘抄
理想的社会
宗教裁判法
对义务教育的批判
社会仿生的原理
新国学的精神
史书重修的一个原则
重修虚幻愚民的历史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