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青生教授,1957年生于镇江。德国海德堡大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艺术史家、艺术批评家、艺术家。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主任、汉画研究所所长。《中国当代艺术年鉴》主编。目前担任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World Congress of Art History)学术秘书长。
由中央美术学院和北京大学共同主办的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将于9月16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世界艺术史大会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联络机构国际艺术史学会(Comité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de l'Art,简称CIHA)与每届大会的主办国联合组织。该会议是国际文化艺术界的重要会议,每四年召开一次,自1873年以来已经举办了33届。这是中国首次主办。
吴可佳:感谢您接收记者的采访。九月份世界艺术史大会即将在北京召开。对于世界艺术史大会的历史渊源我们的读者可能不太了解,能否请您向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
朱青生: 世界艺术史大会是国际艺术研究和艺术史学界最大的会议,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面的分支机构,研究古今中外一切艺术和形象物,每四年举办一次,在各个国家轮流召开,被称为艺术界的奥运会,中国在2005年成为这个国际组织的会员国。
我和同事们在邵大箴先生和范迪安先生的领导下参与了这个工作。我们从2008年就开始试探,看看中国是否主办这样的会。2009年我们正式提出了方案。也有一些竞争者和不同的意见,尤其很多复杂的意见是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相关的决策人也来到中国,与中国各方面的专家接触,他们意识到中国不可忽视。中国有一个缺陷,也有一个巨大的优点。缺陷是中国没有综合性大学的艺术史专业,艺术史专业是与艺术学院靠在一起,就像我们有中文系,中文系与作家协会在一起,因此会受到各方面的质疑。
但是我们提出了一点,就是中国的考古和文物研究是相当出色和发达的。中国艺术学院的艺术史系也有它的特色,特别是当代艺术和评论方面也有特长。另外,我们也出了一张牌,如果中国召开这样的会,就会迅速提高它的专业的发展。
中国在申办的时候又做了一个非常仔细的安排,就是我们怎么来跟世界说我们办什么会、怎么办。那么我们就选择了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有两个针对性,一个是我们现在要说的问题肯定跟我们国家的事情有关,但是又不是我们国家自己的问题,是大家的问题,只不过在我们国家提出来比较好。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过去的艺术和艺术史都是以西方和欧洲的艺术为核心,它的根据是希腊的艺术和希伯来基督教的艺术,这个确实很重要,但是并不全面。很多国家既不是基督教的国家,也不是希腊传统的国家,那么它有艺术,特别是像中国、以及东方,它们的艺术跟这个渊源没有关系,但是它源远流长,而且成绩卓著。那么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过去把艺术和艺术史仅仅看成是西方的概念,它就不全面。我们过去顶多是用西方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别的民族中间可以被研究的问题。但是不可以被研究的问题呢,它无疑会受到忽略和轻视,甚至是歪曲。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不同文化和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和艺术史的考察,这个对所有的人来说,也许都是重要的。
我们提出了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发现自己曾经被压抑和遮蔽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今天是否有别的文化和别的民族的艺术和艺术史被遮蔽和压抑,这样它就变成一个普遍的话题。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有个中间方,他们会说我们有的东西跟你们欧洲也不一样,跟你们东方也不一样,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一方。还有比如说有些国家像巴西,它认为你们说的艺术跟我们都不一样。这样第三种就出来,通过中国的提议,激发了他们的诉求。因此这个会开起来就比较容易会得到大家的支持,后来就很顺利。
我们申办的题目是“Terms”,就是讨论一个概念问题。
吴可佳:当时是如何想到“Terms”这个词的呢?
朱青生:本来我们的意见是“Concept”(概念),但是大家觉得“Concept”这个词在拉丁语词根有一个意思就是要使它凝固成一个概念,但是我们要讨论的概念并不是要它凝固,而是可以诉诸讨论。所以经过几次讨论,各国的艺术史学会的主席和国际艺术史学会的理事都参与了讨论,觉得用一个较为松动和宽泛的词比较好。它也不是纯粹的“terminology”(术语),而是就一个观念、一个概念,我们来看看各个国家具体的艺术是如何体现、如何分配和如何评价的。
吴可佳:回顾您自己与艺术有关的职业生涯,从最早到南京读书、到中央美院、又去德国。您能向我们讲述一下这些经历对于您的艺术研究及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朱青生:我们这一代人是非常特殊的一代,我是77级的大学生,本科在南京师范学院。
80年代我们都参与了思想解放的活动,我本人也参与了很多丛书的翻译等工作,有一个“二十世纪文库”,我就负责艺术学的编委。86年,我负责在中央美院组建了“中国现代艺术档案”。当时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诉求,就是要把模仿西方艺术的方法结束掉,回到自己的传统、根源当中去。87年我调到了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教书的同时,我修完了北京大学古文献专业的所有研究生课程,把文字音韵训诂以及重要的考古课程彻底地做了一遍。我目的很清楚,就是要把艺术和中国古代渊源之间的关系,找到解释和清晰的表述方式。
什么是艺术?艺术有我们要保存文化、接受审美和发扬传统的问题,但是更重要的,艺术应该是开拓人的自由和开放、并且引领和推进文明,这才是最重要的。
吴可佳:您那时在北大已经在做一些和汉画有关的事情了?
朱青生:还没有。研究生毕业以后,我留在中央美院教书,我的专业是西方艺术史,但是由于当时我们对于西方艺术的材料少,所以我们就慢慢把自己主要的力量转向了当代艺术,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这是当时改革开放的需要,也是我们自己精神的取向。我就不再研究西方的古代历史,而是推进当代艺术运动。这个叫八十年代现代艺术运动,当时也还有一个称呼叫“85新潮”在86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意识到,“85新潮”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对西方的模仿应该结束,应该迅速走向原创性阶段。
那时候的艺术叫Avant Guard,叫做前卫。前卫并不是在艺术中间前卫,很多做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觉得思想是前卫,其实前卫是还没想呢,他(她)就跳到前面去了。所以艺术家很特别,这在各个国家都是这样一个情况。他(她)还没来得及想清楚,已经开始行动了。而这种作用恰恰是当代艺术作为人的解放的道路的一个特质。后来的当代艺术几乎从来没有放松和停息过这样一个特质。
这个就是我们在80年代做的事情,后来就遇到了89年的风波,我们就没事可做了,也不能做了。这时候我们很多人就做各种其他的事情,有的人就做生意去了,有的人就出国继续留学。像我的话、包括像高名潞都选择了出国。出国以后就遇到了我刚才所说的事情。
吴可佳:面临选择去哪个国家的问题?
朱青生:对,去哪个国家。我当时有美国和德国可以选,我就选择了德国。就是这样的情况。
我在国外做学位是争取时间,所以我的学位论文的题目是捡来的。 我给自己规定了三条,第一,我对这个题目要根本不知道,碰上了什么就是什么;第二,我对这个题目不感兴趣;第三,我对这个题目没有过任何的先期准备。顺便来看看,在德国这样学术严格的地方,尤其是在当时的海德堡大学,它的艺术史系是极为严格的,它的一个博士论文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当时我的论文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题目。我的隔壁有一个医生,住在我们家附近。他有一批门神的收藏,他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你能不能拿它来做博士论文?我说:“完全可以啊。”因为我被派出去的专业是东亚艺术史,但是我当时的辅修专业是德国当代艺术,研究博伊斯(Joseph Beuys)和他所追随的艺术家William Lehmbruck(威廉∙林布鲁克)。所以这样一来,一个是沿着我过去的兴趣方向接着在推进,一个是也在学习这个方法。
等我再回国的时候,回头想起来,在中国如果要推进艺术史专业,应该做什么事情。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建立“图像数据库”。当时95年我们称它为“图像志”。中国的图像志,汉代是可以建的,因为汉代有很多图,而且有文献。汉代之前也有很多图,但是没有文献;汉代之后呢,关键是汉代得建好了。所以我认为汉代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往前可以推,推到没字儿(文献)的。什么叫图像志,就是有一个图,你要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它在一个空间中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称之为“形象学”。那么后面的呢,最好是越前面的做基础越好。
所以我是回国后才决定做汉画研究所。
吴可佳:今天讨论的话题主要是围绕着两个关系,一个是中国艺术和西方艺术的关系,一个是当代艺术和古典艺术的关系。您开始谈到世界艺术史大会已经涉及到了第一个问题,我们过会再进一步展开。对于第二点,当代艺术和古代艺术,实际上都需要投入大量精力。您能讲一下同时在做这两件事情,并驾齐驱的时候,您从哪个角度来切入?另外这么长时间以来,有怎样的心得体会?
朱青生:世界艺术史大会,这实际上是一个临时的任务。我被我的老师和同事们指派和委托做这件事,担任大会的秘书长,我就应该为大家服务。这个事情跟我们的工作都一致,能够提高中国文化的尊严、引导这个学科迅速地进入中国,为各方的学者及中国的学者建立方便的联络,这是举办这个会的目的。大家一听都觉得挺好。也有少数人反对,他们竟然说我是崇洋媚外,所以才开这个会。我觉得这个说法是非常不对的,我们恰恰是因为中国的尊严才开成了这样的会。大家因为有这样的会对中国更加尊敬、更加理解,而且我们也遇到很多对中国有误解和贬低的人都通过我们的工作改变了他们,至少没有让他们过分嚣张。所以正好是他们(反对者)判断的反面。
这个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几乎是全体人的工作。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那么你问到我的工作恰巧碰到一个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是当代的,这两个事情搅到一个人身上怎么办。我的想法是:作为一个教师、或者是大学的研究者,我的专业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汉代研究。我现在是历史系艺术史教研室的一个教授,我就是做这个的。我过去在艺术学院美术系工作,我也是做这个的。
但是我一直在社会上有个工作,就是从86年开始,一直做当代艺术档案的主编,后来又以档案编成了年鉴,我又继续担任年鉴的主编。这个事情对我来说不是我的专业,是我的一个任务、工作。因为总要有一个人出头来做。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我做,我是带了一群人在一起做,只不过我在建立这个档案的方法和制度上花了很多的功夫、也指导了很多学生论文。
那么当然一个人又做古代,又做当代的话,他必然会分心。对我来说,第一是比较忙,第二是有些事情就会做得慢。倒也没有妨碍质量。我一直认为,我们的研究质量在我们的同行中间,是保持着它的最前沿。好在我有很多年轻的同事,我在和他们一起工作,就非常有意思。
关键字:艺术史,事情,也有,北京大学,研究,汉代,朱青生内容标签: 艺术史 事情 也有 北京大学 研究 汉代 朱青生


献给世界,你的真心,以致来世,以致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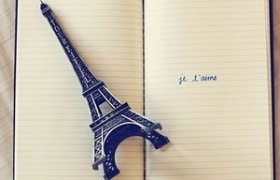


新国学理论
新国学2021年元旦新年贺词
明学与明品生活
文化革命、人类物种与理想社会和人生(一)引言
中医之数理科学化改革与基元系统人体数理模型
新国学的目标及启蒙运动
人性之声HK--悲惨世界
人性与是非善恶
关于美与艺术的内在原理之摘抄
理想的社会
宗教裁判法
对义务教育的批判
社会仿生的原理
新国学的精神
史书重修的一个原则
重修虚幻愚民的历史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