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1998年发表于台北《艺术家》月刊
后改写为《跨文化美术批评》第6章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此处有删节
一、引语
西方的学术,以阐释为主导。在哲学上,两千多年的学术史,可以说是对古希腊哲学的阐释和对这些阐释的阐释。解读(interpretation)是一种阐释行为,对于此行为的研究,便是阐释学(hermeneutics)。本章在批评实践中探讨阐释问题,讨论对象是英国当代艺术家高滋华斯,及其地景艺术(也称环境艺术)中的禅宗精神。
安迪·高滋华斯(Andy Goldsworthy),20世纪末21世纪初最具国际影响的英国观念主义环境艺术家,一九五六年生于彻希尔郡,一九七四、七五年受教于布莱德福美术学院,随后三年求学于普列斯通工艺学院。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环境艺术活动,高滋华斯一直以自己家乡的大自然为艺术源泉和创作场所,并以家乡为中心来扩展自己的活动范围。现在,他的艺术影响已遍及了整个西方世界,并成为当今欧美艺坛的一位热门人物。
面对高滋华斯的作品,我们首先遇到了一个阐释的难题。一方面,两百年前英国湖畔派诗人浪漫诗歌中的自然情怀,可以帮助我们从英国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角度来理解高滋华斯;可是另一方面,高滋华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他的作品体现了后现代时期回归自然的思想倾向,特别是东方禅宗思想在西方的影响,所以湖畔派的浪漫诗魂又不能帮助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理解其艺术。这样,阐释高滋华斯便使艺术批评面临了误读的危险。然而,正是高滋华斯作品对批评的此种挑战,才使我们不得不通过对其作品的阐释实践,来简要梳理西方阐释学的发展历史和当代阐释理论的现状,从而为我们的美术批评提供一个立场和方法的理论依据。
二、阐释的理论:历史与现状
古希腊神话中的神使海尔梅斯(Hermes)往返于神和人之间传递信息,负责解释神的旨意,于是神使之名便成为“阐释学”(hermeneutics)这一术语的由来。在柏拉图的著述中,古典的阐释学已露苗头,但古典阐释学的真正建立,却归功于中世纪希伯莱学者对圣经的阐释,即对圣经文本多层次含义的划分。照当时基督教的阐释,圣经文本份字面含义、道德含义和精神含义三个层次,于是对文本的解读,便在三个不同的层次上进行,这是阐释的深化或升华。随后分层理论更加精细,据说意大利诗人但丁划分了四个层次:字面的、道德的、讽喻的、神秘的。另一种四层阐释理论出现于十二世纪,有字面(历史)层、讽喻(象征)层、转义(道德)层、神秘(末世)层之分。在文艺复兴时期,古典的分层方法,得到了充份发展和完善,并在宗教改革的阐释实践中广泛传播。虽然古典阐释学基本上局限于圣经和相关哲学,但它为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和艺术阐释打下了方法论的基础。
现代阐释学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德国哲学家西勒马赫(Friedrich Schleirmacher,1768-1834),他力图打破宗教哲学对阐释学的限制,主张阐释学的
一般化,并给阐释学下定义为“理解的艺术”。西氏的理论,强调语法(语言)的含义和技术(心理)的含义,也承认理解过程中的顿悟和升华。西勒马赫的传记作者迪尔泰(W.Dilthey, 1833-1910)大大发展了西氏的一般阐释学,他将阐释理论广泛应用
于艺术、法律、诗歌、文献、建筑、舞蹈等领域,通过阐释实践而指出,这一切人文现象都是人类精神的载体。
在起源上对当代阐释学影响最大的是德国现象学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他认为,阐释的行为是人的存在基础,存在就是阐释。他在其巨著《存在与时间》(1927)中指出,所谓理解,实为对自身之存在和存在状况的理解,因而每个人的存在,实际上就是对自身存在的解释。海德格尔的贡献在于,他将传统阐释学和现代阐释学对文本和客体的阐释,转移向了对阐释者自身的阐释,将人的存在方式和阐释方式联系起来,强调了阐释者作为阐释主体的重要性。海氏的理论不仅成为二十世纪西方阐释学的人本主义前提,也给后来的接受理论和读者反应批评提供了理论依据。海德格尔也重新阐释了“阐释的循环”问题。本书第一章第二节已经谈到,过去的阐释理论认为,对具体文本的解释决定于上下文(语境),而上下文由若干的具体文本组成,因而对上下文的解释又决定于具体的文本,这便是所谓文本整体与局部的循环冲突。此冲突着眼于被阐释的客体,而海德格尔则着眼于从事阐释活动的主体。他所谓的阐释的循环,以人往日的存在经验与现时的阐释方式为中心,也就是说,如果阐释者不回到过去的存在状况中,便无法理解现在的存在状况,而不理解现在的存在状况,便又无法阐释过去的存在状况。此循环的历史结构,揭示了人存在于世界的中心地位,揭示了阐释的要诣:艺术是人的历史存在方式,批评是对此一存在方式的阐释。
伽达莫尔接受并发展了海氏阐释理论中关于历史和现时之关系的观点,强调语言在阐释中的重要性,认为真理是艺术中的既存现象。在阐释的循环中,伽达莫尔认为对艺术的理解,需要在该艺术产生时的历史和文化环境,同现在阐释者所处的环境之间,求得“地平线的溶和”,即过去和现在的对话。此对话的关键,是阐释者对自身在现时所处的历史和文化环境的理解,并把握这个环境与作品所处的环境之间的承续性关系。伽达莫尔不承认对艺术作品的所谓最终的绝对阐释,而看重阐释者主体的重要性和历史的重要性,他认为作品的含义是随历史变化的。伽达莫尔关于阐释学的另一重要概念,是“作为地平线的语言”。语言是艺术家对经验的阐释,是作品的客观地平线;语言也是阐释者对经验的阐释,是阐释者的主观地平线。语言地平线的三个特徵是语言的限制性、客观性和相对性。主客观两条语言地平线的溶和,是我们阐释艺术的基本条件。
在伽达莫尔之后,对当代阐释学最有贡献者,是法国哲学家利科(Paul Ricoeur, 1913-)。利科指出了伽达莫尔一派阐释理论的弱点,即在阐释者和被阐释对象之间,忽视了语言对二者之对话的扭曲。因此,利科的阐释学便是对解读的质疑,他认为阐释学是要在文本的谬误陈述中恢复真实,而文本则对是阐释者之谬误的挑战。这样,利科便力图在阐释学和其它学科之间架起一道桥梁,如分析哲学、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神学等等,并以此而将阐释学的焦点,从伽达莫尔的认识论,移向了更有实践价值的方法论。
德国批评家尧斯强调主观的阐释,看重读者在解读实践中的重要性,因而他这一派的阐释方法,就被称为读者反应批评。美国批评家赫希(Eric Donald Hirsch, 1928-)则强调客观的阐释,认为是作者的意向赋予作品以含义。赫希的观点暗示了批评家和作者的矛盾,因为在作者的意向和读者的阅读之间,有一个历史文化背景和个人经历的错位。在七十年代,后结构主义兴起,法国哲学家巴特、福科、德理达等专注于作品的文本性,这在八十年代演化成解构主义思潮,并以“误读”、“误解”之说为理论热点。随后在后现代主义环境中,福科式文化阐释的“谱系发生”理论得以最终确立。由于阐释理论和方法在本世纪后期空前发展,于是九十年代便出现了关于“过度阐释”的论争,介入其间的都是目前学术界最有影响的人物,如意大利哲学家埃科(Umberto Eco,1932-)、美国批评家若迪(Richard Rorty,1931-)和卡勒(Jonathan Culler,1944-)等。埃科的理论依据是符号学,他主张读者的重要性。若迪和卡勒的理论源于实用哲学和后现代主义,他们与埃科的争论告诉我们,阐释学发展到二十世纪末,学者们已开始对阐释这一学术现象本身发生了怀疑,所以对阐释的质疑和辩护便成为人们目前关注的焦点。
三、阐释的认识:高滋华斯的观念性
艺术批评中的阐释,首先涉及到看作品的立场、出发点和视角问题。高滋华斯的作品之所以在西方和日本等地受到普遍欢迎、之所以在当代艺术界学术界和一般文化圈中也都极受欢迎、之所以能够曲高而又和众,是因为他将当代艺术的观念性探索和大众艺术的温馨浪漫情调完美的融合了起来。但是,这种完美融合也可以说是一种狡猾的折衷,典型地暴露了后现代文化之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两面性。高滋华斯的这一特点,提醒了我们对立场问题的警惕。所谓立场,是指我们看作品时所站居的位置,也就是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去看作品,视角就形成了,所以三者实为一体。古人讲知己知彼,我们是若不了解自己的立场,对艺术现象的阐释便会含混不清,甚至自相矛盾。
古典阐释学的分层方法,企图对不同立场进行调和。但是,阐释字面含义,其立场是语法的或文本的;阐释讽喻的含义,其立场是象征的或修辞的;阐释道德的含义和末世的理论,其立场是宗教的。这种层次分割,破坏了作品的有机整体,调和立场的目的便很难达到,这与后来基督教的分裂有直接关系。我们对高滋华斯的阐释,当然可以采用古典的分层方法,但为了不破坏其作品的整体性,我们还是采用多角度围观的方式。
我们可以先从历史的角度看高滋华斯。一九八七年,高滋华斯在日本制作了<
美术史告诉我们,极少主义是对传统雕塑和早期现代主义抽象雕塑的反拨。当卡尔·安德烈(Carl Andre)在一九六六年把一排整齐的火砖平平铺列在博物馆地面上时,他至少有两个目的,一是颠覆往日雕塑的直立性,二是用非制作性来颠覆制作性。由于极少主义仍然保留了材料纯粹的传统特点,波普艺术便针锋相对,混杂地使用现成品。极少主义和波谱艺术是本世纪中期西方美术史的转折,是后期现代主义向早期后现代的发展环节。高滋华斯的作品,一方面继承了波普艺术的现成性、继承了极少主义的材料的自然性,另一方面又既用极少主义的纯粹性来颠覆波普艺术的混杂性、也用堆积空洞的制作工夫来颠覆极少主义的非制作性。高滋华斯在堆积卵石时,按卵石本身影调的深浅顺序,由暗到亮向尖顶推进,让最亮处突然出现一个深黑的洞穴。这既提示了用极少主义的纯粹性来升华波普的杂乱的现成品,又用影调递升的顺其自然和突然出一个洞穴的颠覆行为,来解构了当代美术的发展历史。但这是不是高氏的创作原意,我们不得而知。
黑格尔所代表的古典历史主义,以“目的论”(Teleology)来统一历史,以把握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螺旋式上升规律,主张用当时的眼光看当时的艺术。这种僵硬的历史主义,妨碍了我们用今天的眼光看往日的艺术。高滋华斯的作品,力图从今天的立场出发,去获取一个跨历史的视点,以便将往日艺术同今日艺术联系起来,这同新历史主义以割断历史来反对黑格尔完全不同。如果我们借用伽达莫尔的术语,高滋华斯便扮演了一个美术史的阅读者或批评者的角色,他用解构主义的颠覆方式,把他自身立场的地平线同极少主义和波普艺术的语言地平线融合了起来,既避免了黑格尔的线性历史,又避免了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断面。在这样的历史观意义上阐释高滋华斯的意向,我们就可以说,高氏的艺术是观念的,他的创作是对二十世纪艺术语言之发展的历史反省。
我们再从社会的角度看高滋华斯。如果说历史观是纵向的,社会观便是横向的,二者的交织有助于我们较全面地从事艺术阐释。社会的主体是人,人的存在意义由人际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决定。一九九五年高滋华斯制作了两件类似的作品,一为《大西洋的芭蕾,抛尘》,另一为《大西洋的芭蕾,抛棍》,这两件作品都旨在探讨和体验人际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大约同一时期,他还完成了抛石、抛叶、抛水等作品。抛尘之作将我们带入了世界起源人类诞生的洪荒时代,当时的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在天地之间混沌一片,完美融合。抛棍之作暗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盖文明之进步,以工具的出现为重要标志,树棍是工具的符号。对史前社会的人们来说,工具也是武器,它提醒我们原始和谐的被破坏之虞。人与人的冲突、人与自然的冲突,成了千万年来社会关系的中心。
为了追寻原始的和谐、证实人的原始力量,高滋华斯曾到北极进行过一系列艺术活动。在那里的极度严寒中,他用双手搓制雪条、用双手打制冰砖,他磊建冰雪之墙、堆出冰雪金字塔。无论是他大型的冰雪圆门,还是精巧的冰片构成,都具有震撼人心的自然力量。创作条件的极度艰苦,使高滋华斯有机会展示他的人格力量。他的作品告诉我们,人对自然的介入,贵在顺从自然,此为和谐的前提。在今日技术社会,和谐的介入已不复存在,艺术所追求的和谐,只不过是文化的假面具。由于约请了许多人参与自己的创作,两件《大西洋的芭蕾》,便具有一种戏剧性。我们可以用语言学的术语这样说,这两件作品的内涵是泛指一种社会追求,而外延则是专门针对当代社会的文化问题。内涵与外延之间的张力,显示了高滋华斯作品的象征和讽喻含义,它具有广泛的复盖范围。这样顺水推舟,顺从自然便成为我们阐释高滋华斯的关键。高氏的创作实践,的确十分顺从自然,他在不同季节不同地区制作不同的作品,他的作品不仅在制作过程中时常毁于自然,如坍塌之类,而且在完成后也必定毁于自然。人来自尘土又归于尘土,艺术来自自然也归于自然。
高滋华斯之所以总是在极少主义和波普艺术身上作文章,就是出于他的自然观,这让人想起我国南齐理论家谢赫六法论中的“随类赋彩”之说。如果说历史的阐释揭示了高氏艺术在语言上的观念性,那么社会的阐释便揭示了高氏艺术在内容上的观念性。而实际上,观念性本身,已经打破了内容与形式的传统划分,所以高滋华斯的作品是一个较为完美的自然整体。
四、立场与方法:顺从自然、顺从心灵
从自身文化的承续方面说,英国园林的优久历史和英伦民族热爱自然的传统,使高滋华斯的艺术有了深厚的根基。从外来文化的影响方面说,日本园林设计中禅的构思,使高滋华斯获得了丰富的灵感。高滋华斯的自然观念,深受日本禅宗的影响。这一影响从宗教、心理、哲学、人类学等角度,在历史的纵线和社会的横线中,为我们提供了阐释的第三度空间,即深度的文化阐释。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对高滋华斯作出立体的较完整的理解。
高滋华斯的艺术精神可用一字概括:禅。其精髓是顿悟,它来自心灵与自然的默契。高滋华斯作品的物理现象,是存在时间的有限性。日出日落时的逆光作品,转瞬即逝,如《石沿竹叶》(1991);夜间完成的冰雪作品,会在次日的阳光下消融,如《冰的螺旋》(1995);秋季的红叶黄叶,也会在秋风秋雨中零落,如《榛树上的红色罂粟花瓣》(1992)。时间对作品的如此影响,是艺术家在作品中对时间之有限与无限的沉思,也是对自然力量的沉思。
沉思是禅的方式,是顿悟的前提。从宗教意义上阐释高滋华斯,当然以禅为先导。由于高滋华斯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而日本文化中又具有中国的佛道思想,所以我们用中国传统的阴阳观念来看高滋华思的艺术,也顺理成章。从外在的视觉形式上说,《卵石洞》中的洞是阴的象征,卵石堆则是阳的突现。从玄学意义上说,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一种阴阳转换关系。转换是合一的一种方式,高滋华斯作品的基本精神,就是人与自然的合一。在高滋华斯<
与《卵石洞》类似的作品,区别多在材料上,有些用树叶堆成,有些用树枝堆成,也有用沙石片、冰块、泥土堆成的,如《水潭碎枝》(1991)。从心理学的角度说,由暗到明向尖顶的推进,和顶端突然出现一个深黑的洞穴,是对深层无意识心理渊源的探究,甚至包括了可能的性象征因素。在《木》的第二组作品“土地”中,高滋华斯在红土地上挖出形若女性阴部的深坑,而且阶梯式向深处推进,层层相迭。他也把这种作品,用泥土制作于树身,产生水平与垂直的两种结构方式。按精神分析学的观点,土地是女性的象征,树干是男性的象征,树木来自土地,又反过来在土地上留下自己的印记。男人在土地上耕作播种,赋予土地以生命,而树作为男性的象征,使人与自然有了相辅相成的关系。这也是一种阴阳关系,它把心理和宗教联系了起来。在此,无意识的顺其自然和理性的顺其自然发生了碰撞,其结果便是禅的顿悟。那深不可测的女性洞穴,是自然和心灵的力量之源,是生命循环、往复不息的渊源。
自从海得格尔将人本主义引入阐释学后,所谓现象学的沉思,便将宗教、心理和哲学的玄学联系了起来。当代西方艺评界一般认为,高滋华斯的艺术哲学,是柏拉图主义的。笔者的看法是,柏拉图主义的艺术思想至少有三点有助于我们阐释高氏作品。其一,艺术是来自顿悟的灵感产物;其二,艺术是象征的;其三,艺术有更深的寄托性寓意。新柏拉图主义也同样有助于我们的阐释,因为这种哲学强调一个至高无上的渊源,认为艺术是此渊源的显现。在高滋华斯作品中,这个渊源当然是禅,而顺从自然则是禅在作品中、在制作过程中的显现。不妨这样说,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既是高滋华斯艺术创作的思想出发点,也是我们阐释其艺术的哲学出发点。正是这个出发点,使高滋华斯的艺术脱离了纯粹性象征的现世性,而获得了形而上学的抽象意义。
高滋华斯于冬季在北极制作的冰雪作品,比他的其它作品更具有原始的自然力量,这让人想到居住于北极地区的因纽特人艺术。因纽特人的大型雕塑艺术,是卵石片的堆垒,这与高滋华斯的垒石作品在外观和精神上息息相通,二者都顺从了自然。高滋华斯在为蒙特利尔太阳马戏团制作的沙石拱门《旅行者的拱门》(1997)下,竖立了一个因纽特式的石堆人像,恐非偶然,这与英国史前时期的石阵古迹不无观念的联系。根据考古研究,石阵既是史前时期的太阳祭坛,也是当时人们观察自然的天象台。在文化人类学的意义上说,石阵是心灵与自然相交合的象征。同样,从文化人类学关于原始艺术的发生角度说,高滋华斯在系列作品《木》中对土地、种子、根、枝、叶、树等等的象征演绎,不论是作品外观上的变形也好,还是艺术思想上的超验也好,都推进到了艺术的起源和人类文化的起源,推进到了人与自然的本体。
就以上各方面的阐释,我们可以对高滋华斯的艺术作两点总结。一是顺从自然,二是顺从心灵。在禅境中阴阳相合相易,使心灵与自然得以交流,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两个境界,构成了高滋华斯的艺术世界。
五、禅的阐释:高滋华斯的文化精神
从人文科学的上述若干方面对高滋华斯的文化阐释,都把我们引向了禅。英国当代批评家罗杰·迪金(Roger Deakin)写过《禅与高滋华斯的艺术》一文,发表在一 九九七年英国《现代画家》杂志春季号上。这篇文章主要是记述高氏<
有这样一段话:
部件设计的精确性,旨在达到一个“理念”,即尺寸的精确,但这很难完美无缺。摩托车上并没有制作得无可挑剔的零件,永远也不会有。但是,当你一骑上摩托车,奇妙的事情就出现了,一种神奇的力量会负载你飞驰于乡间。对学术性“理念”的理性理解,在此致关重要。约翰看着摩托车上那各形各样的钢铁零件,越看越不放心,便停车息火。我也观察着钢铁零件,就在那一刻我发现了“理念”。他以为我在观察局部,其实我在思考整体设计。……摩托车是一个系统,一个真正的整体系统。
帕斯格用柏拉图的术语“理念”,来指零部件之间的相互配合,摩托车的效能,来自局部所组成的整体结构。有了这个完整的结构,那些并非十全十美的零部件,便会有效地工作。用阐释学的观点看,这就是在文本和上下文的循环关系中,强调上下文对文本意义的先决作用。禅的顿悟,强调静思默想中的整体把握,即上下文的语境。迪金在对照帕格斯和高滋华斯的艺术时说,请读者试试用“树”和“木”来代替上述引文中的“摩托车”和“钢铁零件”,这段话可以为我们打开高滋华斯禅境的大门。
实际上,《黑石红潭》的两组作品才是高氏禅味最浓的作品。一九九四和一九九五年冬天,高滋华斯对家乡的山石流水有了新的体验,他发现天气、季节的变化,会影响自然物的外观,如岩石的色泽影调变化,这可以说是客观外界在发挥作用。可是另一方面,同时同地的岩石,有的色泽会深一些,有的却浅一些,这可以见出事物的主观因素。主客观双方的统一,使自然物成为人类历史和文明进程的见证。为了强调自己的思考,为了体验主客观的交互作用,高滋华斯在名为“黑石”的系列作品中,把黑色泥碳涂抹在岩石上,让其与环境产生种种对照。涂抹泥碳的制作行为本身,是重要的思考和体验过程。在严冬的酷寒中,他在野外一手戴着手套涂抹泥碳,另一只手藏在身上取暖。两手交替工作的冷暖之别,让他对环境和主体二者都有了生理和心理的双重体验。有的黑石孤零零地处于惨白的荒草地上,作品具有强烈的明暗力度对比;有的黑石处在其它岩石的自然本色的包围中,作品有种文明的人工感。在傍晚的夕阳下,荒草地一片金黄,黑石倔然而立;在远山行云的背景前,黑石显得沉重而神秘。黑石的质感来自它整块的体积力量,荒草的质感,象是出自美国画家怀斯的手笔,这将自然与人工的关系颠倒了过来,造成虚幻的现实。大片倾斜的山坡,压抑着一块黑石,似乎是在向人向艺术家宣告大自然的无比力量。如果说黑石是禅的象征,它存在于客观外界,那么大自然的荒野环境,就为禅的静默提供了沉思的条件,即所谓天籁之境。高滋华斯涂抹泥碳的默默制作,俨若高僧对外物的专注,制作即是体验,在艺术家日复一日的长期观察、沉思和体验中,物我合一,制作工夫将外物移入了内心。艺术家手上的制作,实为内心的观照,这种唯心的超验实践,乃佛家所谓眼观外物而无物,一切尽在吾心中的境界。因此,艺术家对外物的观照,变成了对内心世界的确认。
“红水”系列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高滋华斯把红色岩石粉用手搓入小水潭中而成。那些红色水潭,有的是雨后岩石凹处的积水,有的是小溪边的一处回水,它们外形各异,成为内心意象的种种变形,并具有时空合一的特徵。艺术家的禅思,从关注外物到观照内心,从感受外物到体认内心,从唯物的认识到唯心的默念,有一个沉思默念的时间过程。在禅的体验中,外界宇宙与内心宇宙相合一,自然时间与心理时间也相合一,这是禅的第一个维度。由于艺术家的禅的静默和向内观照,红水的视觉特徵在内心转化为禅的可视之形,它那阿尔普式雕塑的体积,就是禅的显现形态(而阐本身却是一个无形的观念),是艺术家内心观照的对象。在从外向内转化的时间进程中,红水所具有的自然力量,成为禅的意象所具有的心理力量和思维力量,它聚集在阿尔普式雕塑体内,再通过艺术家由内心向外界的反观而释放出来,内心意象与外在意象便建立了联系,于是构成禅的第二个维度。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的交接,便是禅之力量的显现。
在前面谈到高滋华斯的早期作品《卵石洞》时,我们已发现了这位艺术对洞的迷恋。在他的后期作品中,洞以各种各样的外形出现在不同作品和不同环境中。《木》向我们展示了这些洞:平地上挖出的洞,洞中套洞;树干上雕出的洞,有女阴之形;石料堆积的洞、树枝编织的洞、树叶上撕出的洞、冰墙雪壁上掏出的洞;洞中或有石塔、或有冰柱。洞是一个隐蔽的内在空间,它具有容纳的能力。用东方的篆刻术语说,如果洞是阴刻,它够能容纳红水的流入,那么黑石就是阳刻,它是释放禅之力量的金字塔,也是收集自然能量的聚焦点。阴阳合一,是高滋华斯作品的原型,黑石、红水、洞,都是原型的视觉变体,禅意则是原型的精神归宿,是作品的力量源泉。
也许,用福科的金字塔式权力结构理论,来阐释高滋华斯以禅为至高无上之渊源的艺术整体,会有“过度阐释”的牵强之嫌。但是,高滋华斯的作品,或者是外观上有金字塔式的具体结构,或者是各作品间都有着观念的联系。就我的“禅”式直观印象而言,单看高氏的某件作品,他并不比类似的其他环境艺术家们高明多少,如罗伯特·史密斯(Robert Smith)、理查德·朗(Richard Long)、沃尔夫冈·莱伯(Wolfgang Laib)或克里斯·布斯(Chris Booth)等。然而整体地看高滋华斯的某类作品,甚至通看他的各类作品,就会感受到一种内在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作品,却弥漫在整个环境中,并将我们这些看作品的人,也溶了进去。这恰如我第一次看秦始皇兵马俑的感受,那阵列的磅礴气势,弥漫了时间和空间,淹没了一切,让自我溶化在禅的世界里。
六、结语
批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阐释的立场和视角,而阐释的方法在相当程度上也就是批评的方法。西方二十世纪的形式主义批评,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三种具体方法:新批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从罗杰·弗莱和克里夫·贝尔,到格林伯格和劳森柏,无论是西欧还是北美,形式主义方法在几十年中已发展得相当完善。但自20世纪中后期解构主义发难和后现代主义兴起,萝莎琳·柯劳丝(Rosalind Krauss),哈尔·弗斯特(Hal Foster)和亚瑟·但托(Arthur C. Danto)等今日美国最有影响的艺术批评家,则打破了立场和方法的界线。他们与欧洲后现代批评家们遥相呼应,将艺术批评的哲学,从图像分析的时代,引入了跨文化的综合时代。我们在阐释高滋华斯艺术时遇到的难题,应该在跨越东西方文化界线和人文学科界线的实践中,寻求解答。说不定,这是关于二十一世纪之批评与阐释的禅的寓言。
关键字:作品,自然,莫尔,历史,主义,批评,内容标签: 作品 自然 莫尔 历史 主义 批评


献给世界,你的真心,以致来世,以致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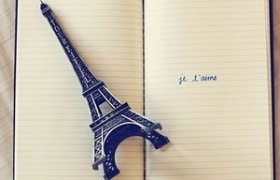
新国学理论
新国学2021年元旦新年贺词
明学与明品生活
文化革命、人类物种与理想社会和人生(一)引言
中医之数理科学化改革与基元系统人体数理模型
新国学的目标及启蒙运动
人性之声HK--悲惨世界
人性与是非善恶
关于美与艺术的内在原理之摘抄
理想的社会
宗教裁判法
对义务教育的批判
社会仿生的原理
新国学的精神
史书重修的一个原则
重修虚幻愚民的历史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