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恶之花
近一两年,中国当代美术界似乎突然发现了加拿大艺术家爱德华·柏汀斯基(Edward Burtynsky),尤其是从事观念艺术者,更对他关于中国之世界工厂的电影表示了惊讶和极大兴趣。其实,柏汀斯基早就发现了中国,他在近十年中,几乎每年都到中国旅行、摄影,特别是拍摄三峡大坝和太湖沿岸的工厂,以人与环境的关系为主题。我于2004年在蒙特利尔当代美术馆,参观过柏汀斯基的大型摄影作品回顾展“人造风景”(Manufactured Landscape),认为其主题是“恶之花”,本文即略谈此问题。
柏汀斯于一九五五年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小镇圣-凯瑟林,后居多伦多。作为摄影家,他出道于八十年代初,现在是北美最走红的摄影艺术家之一。他的作品,以观念手段来诗意化地处理政治主题,具有“恶之花”的特征。
一百多年前,法国颓废派诗人波德莱尔将现代社会的工业发展、人类的道德沦丧以及文化的堕落称为“恶之花”。一百多年后世纪末来临,柏汀斯基以艺术家的敏锐,放眼后现代时期人类经济文明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他以敏锐而精细的眼光凝视自然,用直观的摄影,毫不掩饰地向世人展现了今天的“恶之花”。
按柏汀斯基自己的说法,在他二十多年的艺术生涯中,其一贯主题是工业对自然的改变。他的回顾展作品,按题材分为六部分:一、破碎的大地,二、采石场,三、城市矿场,四、拆船场,五、石油基地,六、三峡大坝。过去我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美术馆和画廊里零星见到过柏汀斯基的作品,但由于其零星,缺乏整体效果,所以印象不深。在蒙特利尔当代美术馆里,直接面对这位艺术家的六十多件大幅作品,因其整体气势,而能看到并感受这“恶之花”的强烈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
二 破碎的大地:审美形式
在修辞学上说,“恶之花”一语是一种反向的矛盾修饰,具有反讽的含意。柏汀斯基象波德莱尔那样,在文明进步和繁荣发展的表象下,看到了人类给自己造就的危险和威胁。同时,他又不同于波德莱尔,他不是一个颓废派艺术家,他在社会的毒瘤和工业的脓疮里看到了如鲜花盛开般美丽的艺术形式,在废物和垃圾堆的细节中发现了妙不可言的色彩。因此,他借反讽的修辞手法,赋予“恶之花”以美和崇高的形式。
“恶之花”的视觉美感,以“破碎的大地”为最。这部分有四组作品,分别是“露天矿场”、“铁路割痕”、“污水流淌”和“民居建筑”。这四组作品的主题基本相似,是采矿、筑路、排污、修建等人类活动对大地的破坏。我们不难看出,这些作品所呈现的,都是人类“恶之花”的邪恶。然而,我们不易了解的是,“恶之花”何以具有如此这般的视觉之美。
加拿大和美国,都以自然风光著称,在两国的摄影中,自然风光是一大题材,美国的风景摄影大师亚当斯,是这类艺术的先驱者。不过,这些前辈风光摄影家,过多关注风景的自然之美,他们是美的捕捉者,而非创造者,更非怀疑者。尽管他们作品中也有人文因素,但要么人文因素太直白,如直接拍摄风景中的人或人的活动痕迹,象原住民的房屋之类,要么人文因素无关紧要,仅是风景中的点缀而已。
柏汀斯基不是前辈意义上的风光摄影家,而是后起的当代观念艺术家。他的风光摄影,将自然之美同新的人文意识天衣无缝地连结起来,使风景不再是简单的风景。此处所说的新的人文意识,是指艺术家对前辈的超越。亚当斯的风景,是用大自然来蕴含诗意的情感,柏汀斯基超越了美的表象和诗意的内含,他的作品是观念的,他在诗意和自然之美中,注入了西方后现代时期的当代艺术观念,这就是艺术对社会和政治的介入,是艺术的批判性。
且让我们先看“破碎的大地”中的“污水流淌”系列(1995)。进了展览大厅,一面墙上挂着一排火红的大场面俯视风景。远远看去,在这些作品的影调深沉的大地上,红色的流水既象火山喷发时岩浆的奔涌流淌,又象艳丽的鲜花盛开怒放,色彩和明暗对比十分强烈。这几幅作品在污水系列中名为“镍水横流”,摄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作品中,被镍矿污染了的大地,一片荒凉,但因影调的深暗,大地的荒凉之感不易看出,反倒衬托出污水的明亮耀眼,从而将人类的邪恶,在视觉上转化为怒放的艳冶鲜花,将艺术家的政治批评,蕴含在邪恶之美的欣赏中。
我们再看“污水流淌”中的另外几幅冬天风景。这些仍为俯视的大场面作品,远远看去,地面象是美国黄石公园或中国黄龙风景区的石灰岩地貌,有着异样的美感。在浅水轻漫的地面上,稀疏的树林有点逸笔草草,竟象中国古代的文人山水画,色调单纯、淡雅、和谐。这些都是摄于安大略省的“铀矿遗痕”。细看画面,那些稀疏而单调的树木,都干枯秃萎了,不少只剩下朽烂的树桩,既象是经历了森林大火之后的残存物,又象是酸雨或病虫害的罹难者,让人想起日本“原爆图”的劫后余生。这是一幅纯粹的风景,我们看不到人,看不到人类的活动痕迹,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幅美丽的颓败,是人类造孽的结果。
什么是人类的造孽?对一个环保主义者来说,工业和采矿造成的地表植被的破坏和污染,便是造孽,例如露天开矿、修建铁路和公路。对一个艺术家来说,人类活动是一柄双刃剑,既创造了辉煌的文化和历史,又破坏了自然的平衡。对柏汀斯基来说,文明之美与自然之美的和谐共处,可以是美好的,但二者却难于和谐共处,若一定要鱼与熊掌兼得,其结果便可能会是邪恶的。也许,这就是“恶之花”的反讽和当代含意。
三 采石场:观念形式
“恶之花”的形式,在“采石场”系列作品中,不仅显现为自然之美,而且也显现为人工之美,即人造的形式之美。大概正因为此,柏汀斯基的展览才名为“人造风景”,尽管这是人的邪恶之手所造就的风景。
艺术中的形式,指视觉形式。现代主义所说的视觉形式,是艺术内部的构成因素,如点、线、面和色彩、构图等等,以及这些因素间的关系。在现代主义之后,当代观念艺术所说的形式,超越了艺术的内部因素,其覆盖面要广得多,涉及艺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就是艺术的存在环境。虽然柏汀斯基是一位观念艺术家,但就他的作品而言,我认为他在文化意识方面介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之间,因为他在利用形式来传递观念的同时,也用艺术之存在环境的观念,来支撑作品的形式。可以说,柏汀斯基的观念,在相当程度上是关于人工形式的观念,是关于人工与形式两方面的观念。
在“采石场”的名下,有三组作品,于九十年代初分别摄于美国的弗蒙特州,意大利的卡拉拉和印度的马克兰拉,都是大理石和建筑石料的采石场。柏汀斯基的这些作品,唤醒了我少时的记忆,我对采石场并不陌生,反而有一种亲切感。文革期间我家一度住在一个采石场附近,我经常去那里看石工们用钢钎铁锤在巨大的山崖石壁上打出一排排整齐的孔,然后沿孔线将石料一块块凿下。也有的象打井一般,在地面上凿出一个球场大小的数丈深石坑。现在站在柏汀斯基的作品前回想,我当年在采石场看到的,是整整齐齐的线性结构。美国九十年代的采石场,与中国七十年代的采石场大同小异,惟有采石工具不再原始,而是电动和机械设备。但是,无论手工还是机器,石工们的工作,都一样是用点的排列来构成线,又用线的起承转合来构成面,而当四面相围时,便获得了一个立体的空间。
“采石场”系列作品中摄于美国弗蒙特州的十多幅“古老的岩石”(1991),便是这种形式组合的典范。如果说自然的形式是不规则的,是天赐之美,那么,采石场的点线面和立体空间,便是规则的形式,体现出人工之美。二十世纪前期的英国形式主义批评家克利夫·贝尔在讲到形式时说,形式因素之间的关系,与人的审美情感相沟通,他称这种形式为“蕴意形式”(significant form)。当我面对柏汀斯基拍摄的采石场大场面作品时,作品中点线面和空间的构成关系,唤起了我少年时代的记忆和情感,对我而言,这些作品便具有“蕴意形式”。
但是,柏汀斯基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式主义者,他是观念的,他将观念与形式揉合了起来。在“古老的岩石”系列中,形式空间的底部,是一潭漂亮的绿色积水,与灰白色或玛瑙色的石壁相映衬,具有贝尔所说的那种线条与色彩的和谐。绿水是静止而安详的,与采石场的机器喧嚣形成对比。细看之下,我发现这静止的绿水虽然漂亮,但却并非清澈透明,而是浓厚稠重的。这让我想起中国现代诗人闻一多的著名诗篇《死水》:“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何至于此?当然是人工的破坏。在我看来,柏汀斯基这些作品中透露出的观念,与闻一多的政治批判有相通之处:“不如让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甚么世界。”因此,对柏汀斯基的人造风景,我想称之为“观念形式”,而不仅仅是“蕴意形式”。
在摄于意大利的“卡拉拉大理石采石场”(1993)系列作品中,观念形式还具有深远的历史感。自古罗马到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代,意大利的艺术大师们,采用当地出产的大理石来雕刻人类的文明史。然而,柏汀斯基向我们展示的采石场,尽管是人类文明史的一幅幅壮美风景,但却不再是自然风景,而是疯狂开采的人造风景。细看之下,这人造风景竟满目疮痍。同样,印度也是一个古老文明的国度,而印度采石场的累累创伤,比意大利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意大利、印度,二十世纪三个不同世界的代表,其美丽的伤痕竟是如此一致,我要说,这便是柏汀斯基“观念形式”的要义。
四 拆船场:崇高的形式
在系列作品“拆船场”(2001)的名下有四组作品,分别是“拆船”、“回收”、“货柜码头”和“废钢再用”,二十一世纪初摄于孟加拉国。蒙特利尔当代美术馆的巨幅展览招贴,便是“拆船场”中的一幅。画面的主体虽是被拆成半截的破船,但其万吨巨轮的高大身躯和咄咄逼人的气势,却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崇高力量。
西方现代美学意义上的崇高概念,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和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1724-1804)。照柏克的说法,崇高之感具有生理和心理基础,来自人想要保护个体生存的欲望,所以,当人面对恐怖或惊惧时,心中便会涌起崇高之感。如果我们接受柏克的说法,那么就可以这样设想:当柏汀斯基来到孟加拉海滩上的拆船场,抬头仰视万吨巨轮的骷髅时,也许感到了惊惧和恐怖。他用照相机代替自己的双眼,客观地记录了面前的巨型钢铁骷髅,向世人传达了他个人心中涌起的主观的崇高之感。
在此,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崇高感究竟是艺术家的情感,还是艺术家面前的对象所具有的审美特征。也许柏克想要说的是,崇高感是二者间的互动所产生的审美情感,艺术作品是记录或展示这一情感的产品。但是,柏克的恐怖之说,似乎将崇高感和美感对立起来了,结果,具有崇高之美的作品,便因自身的逻辑矛盾而不可能存在。与柏克同时代的康德,认为崇高与美是一致的,具有崇高感的艺术作品,以及具有崇高感的客观对象,都给人以审美的心理愉悦。在这个意义上,柏汀斯基的摄影,比较接近康德的陈述。可是问题在于,柏汀斯基不是一个形式主义者,而是一个观念艺术家。
自解构主义以来的后现代艺术理论,非常看重崇高的概念。德里达将他自己关于崇高的概念,建立在反对康德的形式主义之基础上。对解构主义的修辞批评家来说,所谓崇高,就是对作品之形式和含意的超越。换言之,任何作品的形式都不是一陈不变的,任何作品的含意也都不是固定的。解构主义对崇高概念的阐释,与十八世纪的经典定义相去甚远,这有助于我们解读柏汀斯基的作品。
在柏克的意义上说,海滩上的巨大钢铁骷髅是令人恐怖的;在康德的意义上说,摄影家用块面和体积组合成的构图形式,具有审美的愉悦性,作品有着经典的崇高感。但是,柏克和康德是冲突的,恐怖的骷髅不可能给人审美的愉悦,只可能让人感到惊惧。反之亦然,柏汀斯基拍摄的这些美的构图形式,不可能让人感到恐怖和惊惧。这种冲突和矛盾,应证了解构主义式的推断,即,柏汀斯基的审美形式是多变的,其作品的含意是多维的。惟其如此,在美的表象下,巨型钢铁骷髅的“恶之花”才得以成立。我们且看那孟加拉的海滩,在巨人般的船体上,满是红得发黑的肮脏铁锈;被拆开的船舱,暴露出动物内脏似的结构,令人恶心;而废钢烂铁所污染的海滩,更散发出腐臭的气味。我相信,正是由于诸如此类的“恶之花”具有美的表象,才能具有美感的愉悦,才能诉诸人崇高的审美情感。
所以,我倾向于用解构主义的说法来阐释柏汀斯基:这位摄影家之作品的崇高,是美与丑恶之间永无止境的纠缠,是形式与观念之间永无止境的冲突与调和。德里达不承认作品有固定的含意,他说:“含意正被抹去”,柏汀斯基告诉我们,无论作品是“恶”还是“花”,当二者纠缠一体时,其含意也永无止境。
五 三峡大坝:人道的形式
在柏汀斯基的回顾展上,最吸引我的,莫过于名为“三峡大坝”(2003)的近十余幅大型作品。这些作品中,有些我过去见过,曾感叹于摄影家对中国题材的兴趣。这兴趣不是从一个游客的角度去猎奇,也不是用一个局外人的目光去冷眼旁观。柏汀斯基的观察细致入微,在他宏观的大场面中,我们可以发现丰富的细节。远观近察他的作品,我认为,柏汀斯基的形式之美和崇高感,来自他对大场面的把握,而他的批判性,则体现在具体的细节中。
不可否认,柏汀斯基直接表现三峡大坝的作品,可能有歌功颂德的嫌疑,那就是他拍出了长江的气势和大坝的雄伟。这歌功颂德既是对自然之伟大的赞美,也是对人类改造自然之力量的赞美。但是,如果柏汀斯基的作品仅止于此,那么,他不过是一个平庸之辈罢了。只有当我们看他拍摄的三峡移民和城镇拆迁的大场面时,我们才会发现,他并非等闲之人,而是一个深刻的人道主义者。这就是说,他不是一个盲目的唱赞歌者,也不是一个盲目的批评家,更不是一个不问青红皂白,只会路见不平拔刀而起的草莽英雄。也只有在这时,我们才有可能静下心来慢慢欣赏并体会他拍摄的城镇废墟,揣摩废墟底下的历史蕴含和文化意义。
柏汀斯基的人文关怀,不是那种居高临下的慈悲心肠,不是白种人对有色人种的所谓使命感,而是一种介入。当我看到他摄于三峡库区的城镇废墟作品时,我总要想到纽约九一一之后世界贸易中心的那片废墟。九一一前后,我住在纽约西郊,与曼哈顿的摩天高楼隔河相望。那时我常常陪母亲到曼哈顿过周末,世贸中心的双塔,便是我们进城的路标。可是那天早上我在办公室,母亲打来电话,说世贸中心被飞机撞了,此刻正在着火。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但以后进城,的确不见了路标。过了差不多两个月,我们才去看废墟,没想到那时地下仍有浓烟冒出。过去在世贸中心的广场正中,有一座金属制成的大型地球雕塑。九一一之后,这座被砸扁了的千疮百孔的地球,被人们从废墟下刨出来,安置到附近的南码头公园里,成为一座纪念碑。据说,待新的世贸中心建成后,这座纪念碑将会被挪回原处。
柏汀斯基拍摄的三峡大坝,是人类伟大成就的纪念碑,但是,他那精细的双眼,同时也看到了这纪念碑后面的废墟。正是这一切,才使他的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变得具体,变得深刻,进而获得了一种可怕的震撼力量。
我在纽约的大都会美术博物馆曾看到过一个颇得好评的摄影作品展,作者是旅居美国的印度裔艺术家苏班卡·班内吉(Subhankar Banerjee,1967-),其作品是美国阿拉斯加的北极风光。这位艺术家与柏汀斯基相当类似,二者的主题都是自然和生态环境,作品都是大幅彩色摄影,都有整体的震撼气势;二者都讲究形式之美,都具有崇高感,都有诗意的情怀,也都有人文关怀。但是,二者又完全不同。从题材看,前者远离我们的现实世界,甚至远离艺术家自己的生活,因而太空灵,太飘然,太出世。对比之下,柏汀斯基更现实,更贴近我们普通人的实际生活,因而其艺术观念和政治态度也就更加入世,更具有确切的针对性和批判性。
在相当程度上说,纽约的这位摄影家,是对亚当斯传统的继承,而柏汀斯基则超越了亚当斯的传统。早在柏汀斯基刚出道时,他也拍摄过不少亚当斯式的作品。他那时的摄影,让人想起加拿大早期“七人画派”笔下冷峻的北方风景。但是,他对世界的认识和思考,从浪漫主义走向了现实主义,又进一步走向了批判现实主义。恕我使用这几个老而又老的术语,可这是十分确切的术语,因为这时的柏汀斯基,让人想起了库尔贝的《石工》。他不仅拍摄石工,而且更拍摄石工打造的“人造风景”,无论这风景是丑恶的鲜花还是美丽的废墟。
二OO四年十月初稿,二OO八年十一月年修订,蒙特利尔
关键字:形式,采石场,崇高,观念,风景,之美,内容标签: 形式 采石场 崇高 观念 风景 之美


献给世界,你的真心,以致来世,以致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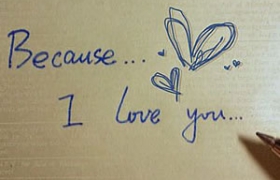



新国学理论
新国学2021年元旦新年贺词
明学与明品生活
文化革命、人类物种与理想社会和人生(一)引言
中医之数理科学化改革与基元系统人体数理模型
新国学的目标及启蒙运动
人性之声HK--悲惨世界
人性与是非善恶
关于美与艺术的内在原理之摘抄
理想的社会
宗教裁判法
对义务教育的批判
社会仿生的原理
新国学的精神
史书重修的一个原则
重修虚幻愚民的历史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