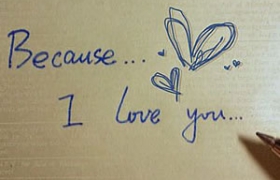艺术家袁佐(左)对话艺术评论家王端廷(右)
每一个人都想要重新界定什么是绘画
王端廷:你在西方接受的艺术教育对你现在的艺术创作有什么影响?
袁佐:80年代的时候,我刚上美院,后来去国外读书,那时候出去的唯一的目的就是想到国外的美术馆去看看原作。我在密尔沃基美术馆(The Milwaukee Art Museum)第一次看到塞尚﹑毕加索等一大批西方大师的原作。1983我叔叔(袁运生)在塔夫斯大学画壁画,他说你过来可以来当我的助手,我就去协助我叔叔在塔夫斯大学了画了一幅27米长的壁画。后来我在波士顿的麻省艺术学院二维空间系上学,因为还是想画画。
我觉得那时候的艺术教育对我影响最深的一点,就是完全打破了我们过去出国之前认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唯一评判标准的认知。从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就是以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为首的一波人,也就是从美国的四十年代五十年代抽象表现主义开始,变成了每一个人都想要重新界定什么是绘画,并且思考今天的绘画是什么样的,我的绘画是什么样的。艺术家都在想自己的绘画应该是唯一的、原创的,从自己的作品开始绘画应有新的语言和新的表现方式。

袁佐作品
王端廷:你说的二维空间系,是将具象的和抽象的都放在一起教吗?能介绍一下吗?
袁佐:学校里一年级的基础课实际上是教你怎样使用各种工具和材料,来表现什么是艺术或者艺术最基本的元素,好比说最基本的元素是点、线、面或者色彩。在一个二维空间里点是什么状态,三维空间里点是什么状态,可以是什么状态,或者说点加上一个时间的话又将会是一个什么状态。这种变化无穷无尽,而且在艺术史的各个阶段,每个人表现点的范例和样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学校很少教授某一种绘画风格。
所以到了后来我到清华美院教书的时候就提出来,基础教学应该是教什么?其实是艺术中的元素、因素、人文背景和工艺材料这四个方面。当你把这四个方面的东西了解了,每个人的解释和运用不一样,将这几方面有不同的组合方式,这就是你的风格,你的风格就会有传承,就会有地域特色,就会有文化判断。

袁佐作品局部
王端廷:有没有对你影响很大的老师?
袁佐:洛瑞·伯吉斯(Lowry Burgess)当时是我们麻省艺术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同时兼任麻省理工学院的高层次视觉艺术中心(MIT Center for the Advanced Visual Studies)主任,这个中心是美国研究艺术与科学最重要的机构,直到现在还是。从60年代末开始这一中心每年提出一个全世界的会议项目。曾经有一年的议题是天空,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创作关于天空的作品。我老师在70年代到80年代最重要的作品是建立新的南极和北极、黑洞和白洞。他曾经给我们上了一个课叫《坐标》,讲你冥想中的空间,臆想中的空间,你的工作室是什么样的空间。他还把我们带到麻省理工的电子望远镜站去看几百万光年之外的星星。现在所有同学一聚会就会谈到那时候学到的空间意识。他开拓了我的艺术观念空间。

袁佐在工作室中
王端廷:那么从艺术本体的角度,如艺术语言和技术层面,你学到了什么呢?
袁佐:在绘画中寻找一种非常自然的平衡、空间的秩序,创建一种新的假想空间。我知道这段学习使我养成了一种习惯,我很难做出一个完全失控的、完全不平衡的,和完全矛盾的作品。我一直认为这变成了我的“弱点”,我想要做一种抗争,一种不和谐的东西。就像这张画上的绿颜色,我在最后加上了两块绿颜色,想保留这种不和谐感,保留这种完全没有道理的冲撞。但是我自己有的时候不敢确定这种东西是不是应该的。我老想到把它改掉,但总是又会回到平衡、秩序中去了。

袁佐作品局部
抽象的本质在于世界内在的真实
王端廷:抽象绘画能不能教?为什么要教?
我把西方现代艺术特别是抽象艺术看作是工业文明时代的象征,一定是跟这个时代的背景相关的。我觉得抽象艺术表现的是我们视觉所看不到的世界,如事物的内在规律、世界的内在的结构,还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物质比如说光。我们能看见的是七色光,就是太阳光谱的那些颜色,但是在太阳光谱之外我们视觉中还有很多的光是看不见的,比如说紫外线、红外线、伽马射线、x射线等等。我们看不到,但是这些东西是物质的,是客观存在的。我们所听到的声音也是有限的,听不见的声音里有次声波还有超声波。这些按理说都属于抽象世界,抽象的本质在我看来是世界的内在本质,也是世界内在的真实。

袁佐作品局部
整个人类文明已经进入到当代,艺术已经有了新的表达方式,比如说行为、装置、影像甚至于虚拟的手段。但是西方现代艺术或者说现代艺术包括抽象艺术在内的这一课,对于中国来说我们都还没有,要想建造当代艺术的大厦的话这些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我还有一个观点就是文明是不能跨越的,我知道抽象艺术在西方已经成为历史了,但是对中国人来讲仍然是新的,这一课我们仍然需要下功夫来很好的重温历史,把它消化吸收,变为我们自己的。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进行抽象艺术创作的一个意义。还有一点就是在我看来西方现在仍然有大量的抽象艺术家在继续推进抽象艺术的创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中国的抽象艺术可能在补抽象历史的课的同时,也在与西方同代的当代抽象艺术家一起探索抽象艺术的新的可能性。中国抽象艺术有这两个使命,一个方面是针对自己的民族艺术的,另外一个是面向世界维度的。
袁佐:我们今天来提倡抽象绘画或是以抽象化的名义来教年轻人绘画思想的时候,实际上更重要的是,通过教抽象绘画来锻炼每个人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方式,或者说是拿过去人们独立思考的经验和结果举例,提出自己的问题和挑战,然后再思考在绘画上怎样去体现。我觉得这在中国的艺术教育中是绝对重要的。

袁佐作品局部
我画的不是美国60-70年代的抽象,而是非具象绘画
王端廷:你判断绘画好坏的标准是什么呢?
袁佐:我认为第一个标准是视觉冲击力,还有一种视觉的原创性。因为我看过的画不少,基本上都能够一眼看到这个东西与众不同之处,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看。我觉得这种感性的直觉是第一位的,其次因为我不是研究些艺术史的,所以我很少愿意去给艺术作品归类,或者说是以区分材料媒介来判断好坏。我觉得视觉给人的感受和直觉冲击力是非常重要的。
王端廷:我认为对于抽象艺术来讲,恰恰需要的是超越感性。
袁佐:当然我说的直觉本能和下意识,是建立在你对文化的判断、修养和艺术知识的建立,以及视觉经验的积累之上的,这些东西你都要有。

袁佐作品局部
王端廷:我也注意到在以往我们的交谈中,你不太使用抽象的概念来界定自己的作品。
袁佐:我还比较忌讳,但不是说反对。因为抽象这个话题在美国已经没有人单独的去谈这个事情了。你把抽象绘画这个话题拿到世界上去谈的话,人家马上想到60-70年代结构主义和极简主义,想到马列维奇、康定斯基之类的。但是实际上中国人想要谈的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可以从抽象艺术作为例子开始谈,或者说引申出去谈。我的画不是美国60-70年代的抽象艺术,我画的挺具体的。
王端廷:那么你觉得如何界定自己的艺术呢?
袁佐:我觉得就叫绘画,非具象绘画。我的笔触很具象,已经不能再具体了。这块颜色虽然是流动的,但我觉得不能再多一点少一点了,到此为止了,只能这样了,所以这是我的较劲儿。

王端廷在袁佐工作室
“后抽象”与“逆抽象”
王端廷:我觉得你不使用抽象这个概念是有一定的道理。其实在我看来,在美国70年代极简主义出现之后,作为形式主义的抽象主义确实已经终结了。就像你说的,已经是一个过时的概念。但是我觉得极简主义之后,仍然有一些艺术家在画一些非具象的绘画,在我看来可以用两个概念来对它们进行描述,一个叫“后抽象”,另外一个概念叫“逆抽象”。所谓的“逆抽象”也可以叫“反抽向”。比如说你的一些作品,用成人画报来进行拼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就是“反抽向”或者称为“逆抽象”。当代中国抽象艺术界热衷于谈论的一些东西,是在抽象表现主义之后加进了一些具象的元素,比如说文字、数字和诗歌中的一些句子,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反抽象”的,就是"逆抽象"的呈现方式。

袁佐用的画笔
袁佐:所以我说的抽象还有两个因素,在极简主义之后不断地还加一些东西,有一种相反的路线比如说抽象艺术一直是走一种简化,从三维空间向二维空间不断地简化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后抽象”或者“逆抽象”又另外加上一些具象的因素、具象的材料,包括拼贴材料、现成品材料等,这都是逆抽象的一个表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中国艺术家来讲,我们现在不必纠结叫抽象或具象,你看我们现在形成的这样一个群体。还有中国的本土的从传统水墨走出来的一些非具象的艺术家,大家实际上是在探讨各自思考中的新绘画意识。
王端廷:我也曾经在文章里提出过一个问题,抽象艺术在极简主义之后还有什么新的可能性?我刚才提到的“逆抽象”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就是状态主义,不是表现形式而是呈现艺术家的生命状态。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种非具象艺术有没有民族性,有没有标准?
袁佐:民族性我不敢讲,但是我觉得它有地域性,地域性能不能归类到民族性里我不知道现在怎么界定。我想可能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莱比锡画派,都是70年代的一波来自东欧的艺术家,做了一些很有力量的尝试。因为大家都是从各个地方来的,大伙都是住在这里,然后慢慢相互影响,我觉得可能是这样一种状态。你刚才讲的状态主义我觉得很有意思,不是民族性的又不是地域的,但是每个人都会相互触碰。

袁佐用的调色盘
宋画的空间关系让我在绘画中走的更远
王端廷:抽象艺术在西方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成千上万的艺术家在这个领域探索耕耘,只是由于中国的这个信息的不对称,我们只是知道西方最有名的抽象艺术大师的一些名作。大量的不太著名的抽象艺术家的成果我们不了解,所以在抽象艺术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很尴尬的事情,那就是“撞车”。这个撞车不能一味的说我们模仿和抄袭,而是抽象艺术相对于具象艺术更容易撞车。具象艺术是我们可见的世界,你画不同的题材,我画不同的变化,都不会撞车。但是抽象艺术是由经验构成的非具象的世界,要想创造出独一无二的个性来,确实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有很多抽象画家不约而同的他会画出相同的形状和相同的画面,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西方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撞车的局面。曾经有一个美国的批评家叫瓦尔特·罗布森,他发明了一个概念叫做“僵尸形式主义” 指的就是西方的抽象表现主义,变成了一种装饰化的创作方式。所以在中国,有很多虽然不是完全一样,但是差别不大。这种现象很多,那么在你看来,中国抽象艺术的独创性到底体现在哪里,它的成就到底要如何评价?

袁佐作品局部
袁佐:我不能讲整体,就说说我自己吧。85年霍克尼到哈佛大学来做讲演,那时候他刚开始崭露头角。他讲到用宝丽来拍了一张桌子的6个面,然后他又拼贴成一张展开的桌子。他提到,毕加索是学了中国的山水画,才画了他那张哭泣的女人,为什么他能同时看到她正面的鼻子和眼的下面,同时可以看到左面和右面,几个面都能看到。这就像中国山水画那样,在卷轴中,能看见山的最下面有个人在划着船,山的中间有人骑着小毛驴在山道上,山的最顶上有鸟在飞也有云,一张画面上是全景式的,所有地方都能看到。他说我从中国绘画和毕加索哭泣的女人里面,体验到了这样的空间关系,所以才做了这张桌子。
我就觉得在我的绘画里,我想讲的就是中国画中的这种空间意识,具体是什么我现在讲不好,但是我就是特别注意去看中国画。我的画呢,在西方他们都认为很有东方韵味很空灵,到了国内,他人们又认为非常美国。所以我觉得可能在我的绘画里头,我想坚持的是中国传统里面的这种空间意识和空间关系,在中国传统绘画里找这种古人的传统意识,特别是宋人绘画里的空间关系,然后借助我的修养和视觉经验来创造今天的绘画。我希望我这样做可以在中国当代绘画中走的更远。

袁佐作品局部
想让画面更混乱一点,更激化一点,更不平衡一点
王端廷:你对现在的创作状态满意吗?
袁佐:不满意,我觉得我每天坐在这里打哆嗦,紧张的不知道要干什么好,天天这样。比较偶然的几张,就那几张东西出来的时候我觉得突然眼前一亮,但是我马上意识到会流于一种状态。我就想要避开,但是一脱开就不知道要去哪。
王端廷:你说对现在的状态不太满意,那么你想改变或者是想变成什么状态呢?
袁佐:我想更混乱一点,更出其不意一点。我不想回避文学故事,我注重所谓的空间速度。我想让画面更混乱一点,矛盾更激化一点,更不平衡一点。现在觉得就是太平衡了,太稳了,我想冲撞一点。我老想说用点黑颜色,但是我从来没用过,想试一试。我想用点黑颜色和很重的颜色,或者是非常不漂亮的颜色,特别肮脏的东西,我觉得我的工作室里太干净了。

袁佐在作品中用到的黄色
王端廷:我看你有一些自己偏爱的颜色。
袁佐:对,黄颜色总是去不掉。我们被训练得画得太漂亮了,画得太美了。好比说画一个人体,不用看一出手就会画得特别美,我这里有一大堆素描我都觉得画的太美了。
王端廷:最后谈一下你最近的创作?
袁佐:像是这张画的是苏州的留园,之前在留园画过很多半开纸的速写画。我想利用留园的那种空间关系,有一点点这种元素的痕迹在一个画面中。有的时候也想借助点曲线或面,把在速写中那些非常随意的和即兴的东西加入我的作品里。这次展出的作品中除了油画,还有丝网印刷、有激光切割等等。在这些拼贴作品中,我拿《Playboy》成人杂志进行拼贴,我把所有的敏感位置都非常当心的掩盖掉了,我想强调的不是性本身,而是想让大家关心色彩与对比,层次的空间的建立,以及运动方向,画面疏密等传统绘画的语言关系。(图文编辑/孟媛)

Local Metaphor 201701-2

袁佐的拼贴作品

袁佐的拼贴作品

袁佐的拼贴作品
关键字:具象,抽象,绘画,艺术,拼贴,艺术家,空间,内容标签: 具象 抽象 绘画 艺术 拼贴 艺术家 空间

献给世界,你的真心,以致来世,以致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