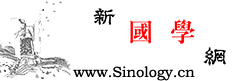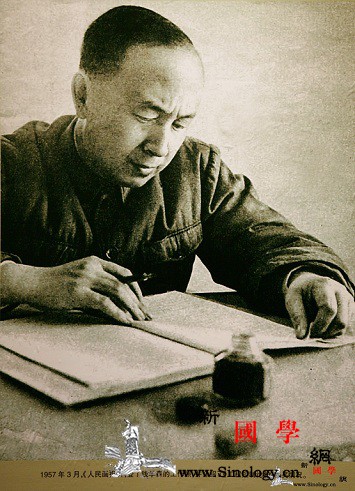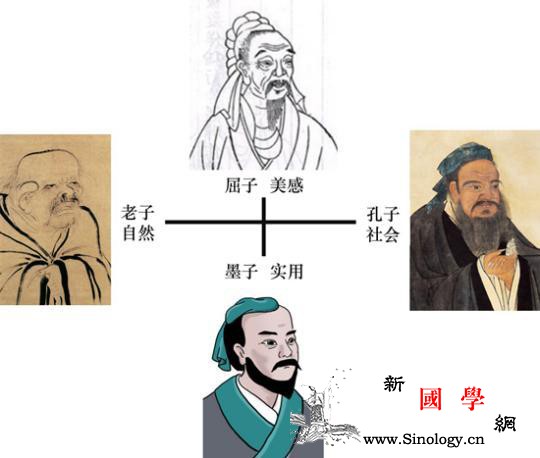新国学网:冀运鲁|史精浩|王政:儒家思想为内核的“前置观念”与古典戏曲解释学研究报告
| |

 新国学网(www.sinology.cn)的新国学理论&新国学启蒙运动&理想社会&文化整理四大板块(本网站中,新闻类未标注版权声明的板块除外),文章都做版权声明和保护(使用/引用观点理论者也请注明《新国学和基元学》双重字样的出处),未经同意和授权就转载者,将视为同意支付每篇文章不低于50万元人民币的稿酬/版权使用费/且收取每点击阅读一次100元的计次费。使用/引用而未注明出处者,也将视情况予以法律追责。凡是转载/引用/使用而引起纠纷者,因本站已经声明在先,故而视同被告同意由新国学网及其有关人员以约定在先原则自主便利地选择起诉地和管辖法院。New Sinology Website(This Website-sinology.cn)'s New Chinese Studies Theory & New Chinese Learning Enlightenment & Ideal Social & Cultural Organisation (except for the section on news, which is not marked with a copyright statement), articles are copyrighted and protected. (use/quote theory) Please also indicate the source of the double word "New Sinology and Cosbu". Those who reprint without consent and authorization will be deemed to agree to pay the remuneration/copyright usage fee of not less than RMB 500,000 per article. The fee for reading 100 yuan per click is charged. Those who use/quote but do not indicate the source will also be subject to legal blame as appropriate. Anyone who causes disputes due to reprinting/citing/using, because we and the site has already stated first, it is deemed that the defendant agrees that we and this website and its related personnel had gained the rights to choose the place of prosecution and the court of jurisdiction by the principle of prior agreement.14264
新国学网(www.sinology.cn)的新国学理论&新国学启蒙运动&理想社会&文化整理四大板块(本网站中,新闻类未标注版权声明的板块除外),文章都做版权声明和保护(使用/引用观点理论者也请注明《新国学和基元学》双重字样的出处),未经同意和授权就转载者,将视为同意支付每篇文章不低于50万元人民币的稿酬/版权使用费/且收取每点击阅读一次100元的计次费。使用/引用而未注明出处者,也将视情况予以法律追责。凡是转载/引用/使用而引起纠纷者,因本站已经声明在先,故而视同被告同意由新国学网及其有关人员以约定在先原则自主便利地选择起诉地和管辖法院。New Sinology Website(This Website-sinology.cn)'s New Chinese Studies Theory & New Chinese Learning Enlightenment & Ideal Social & Cultural Organisation (except for the section on news, which is not marked with a copyright statement), articles are copyrighted and protected. (use/quote theory) Please also indicate the source of the double word "New Sinology and Cosbu". Those who reprint without consent and authorization will be deemed to agree to pay the remuneration/copyright usage fee of not less than RMB 500,000 per article. The fee for reading 100 yuan per click is charged. Those who use/quote but do not indicate the source will also be subject to legal blame as appropriate. Anyone who causes disputes due to reprinting/citing/using, because we and the site has already stated first, it is deemed that the defendant agrees that we and this website and its related personnel had gained the rights to choose the place of prosecution and the court of jurisdiction by the principle of prior agreement.14264
- 下一篇:义工招募 |
- 上一篇:徐文兵:很多中医人没真正弄懂:性、味、归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