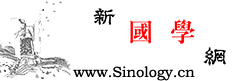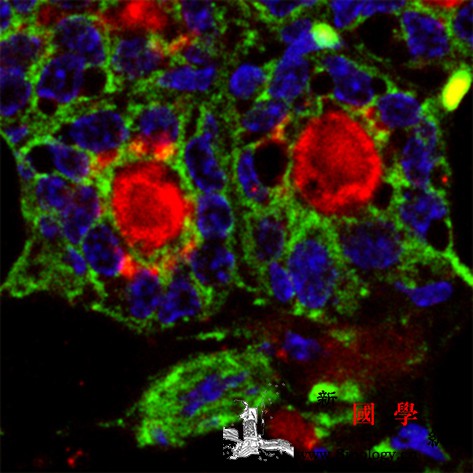东亚地区典型的社会阶段性变迁是夏代盟主制和汉代集权制,文化的汇聚和成型也集大成于夏代和汉朝,夏代的彝文(彝文、夷文、蝌蚪文或当代彝族文字的古文)和汉代的汉字(成熟可用文字、本质区别于甲骨文、金文、篆书等)是代表。

这样,无论是社会体制还是文化成型标志之文字,盟主制夏代和皇权制汉代,都可以作为本质区别的节点和象征,汉夏之文明,当是真正区别于华夏之无妄。周代之诸华,无非是夏代模式之延续而不能作为阶段标志,更何况华之内涵已被后世近代或篡改或误解地扭曲成特定黄种人的标志,高举成民粹主义的政治宣传口号,近代社会学才在东亚社会出现的民族之名词概念被清末民初的狭隘学者已经严重扭曲了历史的真实面貌,所以使用汉夏文明取代华夏文明,将“华人”这个人为的、政治性的、自相矛盾的错误概念恢复到历史真实面貌,将汉族这个错误概念恢复成汉人之本貌概念,实则是重中之重,汉人之概念,无论从人种、文化还是文字方面,非但包含了黄白人种,广义上更包含了西南蛮夷甚至朝鲜日本等漫延区域的文化习俗,是夏代之升华与延续,是山海经所述之广义地理天下观的正统延续,远非狭隘民粹的周代儒家中原华人之概念定义所能包含的,能将汉人分支之一的华人升格至汉人之上,也算是儒家往圣遗传下来最厉害的绝学了,厚黑谋略性大忽悠非儒莫属。

文献方面,山海经是古彝文的汉字翻译之文献,周代盟主制时期的周易等文献也是在夏商文化基础上的金文翻译作品,并且还因文字变迁和孔儒焚书等原因而出现了严重的文化断代,由此缺乏了天文地理科技历史等方面的记载。
河图洛书山海经等等让后世迷惑的文献,其本质是文字变迁、翻译和转述等方面出现的失误和遗失,对比现有彝文记载和中原等地考古文物之蝌蚪文等,可以发现上述史实和线索。

所谓的华夏文明之华,不过是周代盟主制的别称,古文献中出现的诸夏、诸商、诸华之名词就是例证。古代之蛮夷称呼,实质上是将诸华之势力与夏商之势力的区别甚至胜利者的鄙视。
夏商周时代,黄种人和白种人在以中原为地理重心的东亚大范围区域的杂居融合,共同形成了汉夏文化,直至汉朝末期晋朝末期时,白种人尚有逐鹿中原而取代中原天下共主的思维,号称延续“汉统“。
历史发展至唐朝时期,白种人依旧与黄种人一样依然是合法正当的东亚原住民,李白等人是典型的白种人,唐朝皇帝李世民等等,按照古代记载也未必是纯种的黄种人。
所谓的华夏之说法和明清以来批量篡改过的相应史书,大多是儒学盛行之明清时期的产物及其对当代的影响。
总之,汉包含了华,华不过是汉的一个分支。汉夏文明之内涵,囊括了东亚地区,其波及范围、内涵和确凿历史远大于内涵狭窄的所谓华夏,山海经之地理记载,述及了极寒之地(至少达到西伯利亚靠近北极之范围),乃是汉夏文明现存的首推古代典籍。
近代关于中国及民族之概念定义、内涵及其叙述,因旧军阀、民粹主义等利益集团之驱动,存在诸多不尊重史实、疑问、自相矛盾和重大问题。
炎黄子孙之说,是可延续,因无更古而久远用于考证的事物,其中也当含更多之内容。




 新国学网(www.sinology.cn)的新国学理论&新国学启蒙运动&理想社会&文化整理四大板块(本网站中,新闻类未标注版权声明的板块除外),文章都做版权声明和保护(使用/引用观点理论者也请注明《新国学和基元学》双重字样的出处),未经同意和授权就转载者,将视为同意支付每篇文章不低于50万元人民币的稿酬/版权使用费/且收取每点击阅读一次100元的计次费。使用/引用而未注明出处者,也将视情况予以法律追责。凡是转载/引用/使用而引起纠纷者,因本站已经声明在先,故而视同被告同意由新国学网及其有关人员以约定在先原则自主便利地选择起诉地和管辖法院。New Sinology Website(This Website-sinology.cn)'s New Chinese Studies Theory & New Chinese Learning Enlightenment & Ideal Social & Cultural Organisation (except for the section on news, which is not marked with a copyright statement), articles are copyrighted and protected. (use/quote theory) Please also indicate the source of the double word "New Sinology and Cosbu". Those who reprint without consent and authorization will be deemed to agree to pay the remuneration/copyright usage fee of not less than RMB 500,000 per article. The fee for reading 100 yuan per click is charged. Those who use/quote but do not indicate the source will also be subject to legal blame as appropriate. Anyone who causes disputes due to reprinting/citing/using, because we and the site has already stated first, it is deemed that the defendant agrees that we and this website and its related personnel had gained the rights to choose the place of prosecution and the court of jurisdiction by the principle of prior agreement.3990
新国学网(www.sinology.cn)的新国学理论&新国学启蒙运动&理想社会&文化整理四大板块(本网站中,新闻类未标注版权声明的板块除外),文章都做版权声明和保护(使用/引用观点理论者也请注明《新国学和基元学》双重字样的出处),未经同意和授权就转载者,将视为同意支付每篇文章不低于50万元人民币的稿酬/版权使用费/且收取每点击阅读一次100元的计次费。使用/引用而未注明出处者,也将视情况予以法律追责。凡是转载/引用/使用而引起纠纷者,因本站已经声明在先,故而视同被告同意由新国学网及其有关人员以约定在先原则自主便利地选择起诉地和管辖法院。New Sinology Website(This Website-sinology.cn)'s New Chinese Studies Theory & New Chinese Learning Enlightenment & Ideal Social & Cultural Organisation (except for the section on news, which is not marked with a copyright statement), articles are copyrighted and protected. (use/quote theory) Please also indicate the source of the double word "New Sinology and Cosbu". Those who reprint without consent and authorization will be deemed to agree to pay the remuneration/copyright usage fee of not less than RMB 500,000 per article. The fee for reading 100 yuan per click is charged. Those who use/quote but do not indicate the source will also be subject to legal blame as appropriate. Anyone who causes disputes due to reprinting/citing/using, because we and the site has already stated first, it is deemed that the defendant agrees that we and this website and its related personnel had gained the rights to choose the place of prosecution and the court of jurisdiction by the principle of prior agreement.3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