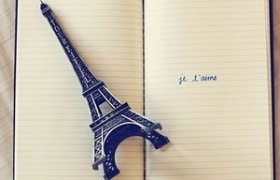自古以来,人类文明社会都会对文化建章立制。文化规制缺失可能会导致文化污染严重和文化暴力盛行,而文化规制过严则可能致使人们的文化生活单调和文化免疫力低下,进一步拉大文化鸿沟,并且加剧因文化冲击所引发的文化危机。虽然文化规制具有一定的内在合理性,但如果文化规制不当的话,不仅无助于文化发展繁荣,而且还可能成为文化危机的导火索。从长期来看,一国的文化规制水平决定着该国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换句话说,文化规制模式的选择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文化战略问题。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现状
总体而言,现有的主流规制理论,例如公共利益规制理论、利益集团规制理论、可竞争市场理论,都不能全面和系统地解释文化规制问题。事实上,时至今日,人们对文化自由问题的兴趣也一直远多于对文化规制问题的关注。因为总的来看,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自由度都不容乐观。这种社会现实在学术研究上的反映就是,同关于文化自由的浩如烟海的研究成果相比,关于文化规制的研究却显得十分薄弱。我们对“EBSCO数据库”“Emerald数据库”等权威外文数据库的文献检索就发现,虽然有关文化规制的思想由来已久,但大多数学者要么是从批判的视角来看待文化规制,要么则将目光聚焦于具体领域的具体文化规制问题。其中,又以媒介领域的规制问题为主,直接以文化规制为题的研究却凤毛麟角。
肯尼思·汤普逊(Kenneth Thompson)主编的《媒介与文化规制》尽管看似是研究文化规制的著作,该书也确实从政治、社会和经济视角探讨了文化政策问题,并涉及到在文化多样性和全球文化产业时代的文化规制“度”,以及文化规制的形式及其竞争等问题。然而,该书的媒介色彩比较浓,也没有涉及到文化规制的许多关键问题。肯尼思·戴森等人(Kenneth Dyson)为《西欧广播与新媒体政策》撰写的第3章《西欧的规制变迁:从国家文化规制到跨国经济治理》虽然涉及到国家文化规制问题,但主要内容是通过比较和反思英国、法国、西德的典型案例,从而分析和解释西欧广播与新媒体政策的发展,与文化规制相关的内容其实并不多。
同宏观的文化规制问题相比,媒介规制问题显然更为热门。就著作而言,主要有从法学视角对媒介规制的研究,例如威廉·弗朗索瓦(William Francois)的《大众媒介法律法规》;对具体领域媒介规制的研究,例如戴维·博勒(David Boller)的《电子媒介规制与第一修正案》;对区域一体化组织媒介规制问题的研究,例如米歇尔·杜佩恩(Michel Dupagne)的《欧盟的媒介法律法规》;对具体国家媒介规制问题的研究,例如路易斯·特奥多罗和罗莎琳达·卡巴特耶(Luis Teodoro & Rosalinda Kabatay)的《菲律宾的大众媒介法规》。这些著作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媒介规制领域的研究成果。
期刊论文反映出的情况也很类似。西莉亚·阿尔达纳(Celia Aldana)直面媒介经常面临的两难境地:虽然媒介设置的议题引发了讨论,并且在建构公共领域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但媒介鲜有机会成为公众议程的一部分。她怀疑,媒介真的有助于促进平等吗?媒介应该成为公众议程的一部分吗?媒介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如何扮演好媒介的角色?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保罗·柯林(Paul Cowling)解释了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具有本土主义色彩的公共利益原则及其在媒介所有权规制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关于国家电视台的所有权规则。这就从银行与反托拉斯、民族主义、联邦主义、媒介规制的历史经验乃至当代关于媒介所有权的争论等多个视角解释了这个谜一样的本土主义概念。他对媒介所有权规制问题的研究也为我们打开了研究文化规制中的所有权问题的一扇窗。曼纽尔·帕皮斯(Manuel Puppis)注意到了越来越受关注,甚至可能动摇西方民主国家媒介规制基石的全球媒介治理中的自由贸易问题,并深入分析了《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关于媒介社会性规制的内容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新公约的影响。从媒介规制的既定规则入手分析规制的实际效果,显然有助于更好地反思媒介规制内容的合理性。曼纽尔·帕皮斯的另一篇论文《媒介治理:分析媒介政策与媒介规制的新概念》则从媒介治理的视角研究了媒介政策与媒介规制问题。但他的主要笔墨放在了澄清关于媒介治理的概念上。他认为,媒介治理之所以争议颇多,不仅是由于这一概念为媒介部门的制度安排提供了综合性视角,因此很具有启发意义,而且在于这一概念能够适合于多种理论研究方法。他的这一思路对我们从文化治理的角度研究文化规制问题很有启发。
就国内的文化规制研究现状而言,同国外的情况十分相似。总的来看,虽然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研究文化规制问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要么是从文化自由视角的批判研究,要么是蜻蜓点水似的零散论述,要么只涉及具体领域的规制问题,系统研究文化规制的理论研究成果依然不多。概括起来,目前的文化规制研究呈现出以下五个特点:
第一,文化规制的研究成果少。虽然文化规制的历史悠久,但历史上的很多人都深受其害,因此,同关于文化自由的众多经典论著相比,专门研究文化规制的成果屈指可数,且大都从文化自由的角度进行批判性研究,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文化规制的合理性。
第二,基本概念尚未梳理清楚。虽然很多学者都在使用文化规制或文化管制的概念,但很少有人对文化规制概念进行清楚的界定。不少学者都将以直接的行政干预为特点的文化规制混同于以间接的参数干预为特点的宏观调控,甚至将文化规制等同于文化保护。
第三,相关研究成果缺乏深度。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人们对文化规制的认识也不断深入。但由于问题敏感,文化规制的相关研究大都“点到即止”,既没有梳理文化规制的基本动因,也未分析文化规制的合法性问题,更少有提出具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第四,放松规制基本成为共识。尽管还有一些学者将加强文化规制作为应对文化冲击和维护文化安全的战略选择,然而,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在新的开放条件下,只有通过放松文化规制,用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办法才能真正应对文化冲击和维护文化安全。
第五,媒介规制成为研究热点。虽然专门研究文化规制的成果不多,但关于媒介规制的研究却不少见。其中又以国外经验、规制现状和规制改革等内容,尤其是书报审查、制播分离和网络规制等具体问题的研究居多。因此难免就事论事,不易跳出思维定势。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就是一个从“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的放松规制的历史过程。问题是,在中国文化规制的指导思想和规制实践上,依然长期未能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传统规制模式。但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和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文化规制必须寻找新的规制哲学,才可能有效应对新技术和新观念带来的新挑战。因此,中国学术界亟需以“为何规制、规制什么、怎样规制”为主线,加快文化规制学的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
二、为何规制:文化规制的类型与缘由
从文化规制的生发演化历程来看,有两种类型的文化规制生发路径:一种是自生自发的文化规制,一种是理性建构的文化规制。
自生自发的文化规制是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的自发生成的产物。在人类交往的过程中,文化规制的作用十分重要。这是由于,社会因合作而出现,合作的基础又在于信任。因此,随着人类合作的范围从基于亲缘关系的合作扩展到大量没有亲缘关系的合作,作为“公共知识”的文化规制就成了降低文化交往成本,增加信任度并以此提高合作效率的有效机制。形象地说,文化规制就像人类交往的“润滑剂”,人类被卷入文化规制的过程(规制者对微观文化主体实施的文化控制)则像“将野兽关进笼子”的过程。事实上,实践中的文化自由往往是通过文化规制来界定,文化规制的意义就是在追求文化自由的推力和约束文化自由的压力之间寻找到处于相对平衡和稳定状态的文化均衡点。在这个文化均衡点上,个人既能够实现自己的部分文化自由,又不会因为自己的言行侵犯他人权益,从而“最小化”整个社会的文化交往成本。一旦这种文化均衡被打破,那么,总有一些强互惠主义者会挺身而出,因为他们“看不惯”和“不舒服”。他们甚至无需任何物质上的激励,仅仅依靠来自大脑尾状核的自我激励机制就能够拥有足够的动力。当然,他们的行为不仅包括“替天行道”式的利他惩罚,而且包括因为看不见摸不着的“信念”所做出的很多看似“非理性”之事。同样,也会有人因为文化规制的束缚而感到压抑和难受,并且想方设法争取更大的文化自由空间。这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
事实上,文化规制的生发演化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历史过程。在人类社会早期,这些具有“文化正义感”和“文化责任感”的强互惠主义者实际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文化规制者角色,尽管所谓的“正义”和“责任”都是相对于他们的价值观而言。他们对不遵守社会文化规范者的利他惩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文化变迁的路径。虽然当今的文化规制已经由人类社会早期以“强互惠主义者和被规制者”为主的文化规制格局演化为了以“拥有规制权的规制者和被规制者”为主的文化规制格局,但强互惠主义者在文化规制中的作用仍然不可小觑。事实上,在文化规制的生发演化过程中,强互惠主义者及其强互惠行为始终对文化规制的生发演化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也是文化规制同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的重要区别之一:并无直接利害冲突的人为了社会文化传统甚至看不见摸不着的“信念”,挺身而出维护文化秩序,主动扮演文化规制者的角色,对违规者实施利他惩罚——自己没有分文好处,却要承担惩罚成本。不仅卫道,甚至殉道。这其实都是人类经过若干代才演化出来的一种大脑自我激励机制,强互惠主义者能够从这种在他们看来“有价值”的行为本身获得满足。这或许正是人类大脑深处仍然留存下来的来自祖先的文化烙印之一。
理性建构的文化规制是个体有意识(individual consciousness)的刻意设计的产物。理性建构的文化规制之所以会出现,来源于两种文化规制观:一种是一元主义文化规制观,这种文化规制观只承认某种文化是“先进”或“正确”的文化,其他的文化都是落后、腐朽甚至邪恶的,因此,对异端文化的规制就具有了所谓的“天然合法性”。另一种是实用主义文化规制观,这种文化规制观不关心某种文化先不先进,正不正确,而只关心实际后果。即使一种文化“先进”而且“正确”,但只要会带来不利的后果,那就应该予以规制。相比之下,一元主义文化规制观主要侧重于价值判断层面,实用主义文化规制观则主要侧重于事实判断层面。一元主义文化规制观和实用主义文化规制观的共同点在于,二者都自负地相信自己的理性,相信文化规制是“管用”的。
理性建构的文化规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信息也是不完备的,而社会是不断进步的,认识也是不断深化的,因此,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化规制史,一以贯之的文化规制可谓凤毛麟角。绝大多数文化产品和服务之所以会被规制,深层次的原因并非在于内容或者形式本身,而是因为不合时宜或者不合地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很多文化规制案例都颇富戏剧性。例如,1955年,法国奥林匹亚出版社(Olympia Press)出版了弗拉迪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小说《洛丽塔》(英文版)。1956年,法国政府宣布《洛丽塔》一书为禁书。1957年,法国巴黎行政法院(Administrative Tribunal of Pairs)宣判奥林匹亚出版社胜诉,《洛丽塔》一书解禁。1958年,法国最高法院(Court of Cassation)宣判法国政府胜诉,《洛丽塔》一书再次被禁。虽然奥林匹亚出版社已经没有了上诉的可能,但由于法国最高法院的禁令只针对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版的《洛丽塔》,而没有要求禁止法国加利玛尔出版社(Gallimard Press)出版《洛丽塔》,于是,1959年,《洛丽塔》又一次在法国面市。就在同一时期,1955年,英国海关宣布《洛丽塔》为禁书。1957年,美国海关则判定《洛丽塔》不属于禁书。因此,在1958年,从法国出口《洛丽塔》是非法的,而美国进口《洛丽塔》却属合法。总之,由于人经常会“犯错”,因此,对于理性建构的文化规制而言,文化规制者切不可过于自负地相信自己的理性,也不能过于迷信文化规制的实际效果,应该掌握分寸,不要过于严苛,而是适度规制,以便日后纠错。
三、规制什么:文化规制的边界与边域
经验地看,文化规制的边界并不总是一条泾渭分明的“线”。无论从规制者的角度来看,还是就被规制者的角度而言,文化规制都有两条边界:一条是文化规制的物理边界,另一条是文化规制的心理边界。所谓文化规制的物理边界,即文化规制的法定边界,是指规制者依据法律授权能够实施的文化规制边界。所谓文化规制的心理边界,即文化规制的心理底线,是指规制者或被规制者根据自己的认知所判定的文化规制边界。由于这两条文化规制边界的存在,使得文化规制的现实边界变得非常复杂。因为规制者和被规制者关于心理边界的分歧,显然很容易直接导致文化规制现实边界的冲突。
如果图1、图2和图3中的心理边界是指规制者的心理边界。第一种情况是文化规制的物理边界大于规制者的心理边界的情况(见图1)。例如,由于突发事件的出现和文化公权力的异化等原因,规制者并不认同文化规制的法定边界,而是根据自己的认知判定法律规定的文化自由范围偏宽。这种观念反映到文化规制实践上,就很可能是规制者的强化规制甚至肆意妄为。第二种情况是文化规制的物理边界小于规制者的心理边界的情况(见图2)。例如,由于思想观念的解放和制度变迁的时滞等原因,规制者并不认同文化规制的法定边界,而是根据自己的认知判定法律规定的文化自由范围偏窄。这种观念反映到文化规制实践上,就很可能是规制者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第三种情况则是文化规制的物理边界恰好等于规制者的心理边界的情况(见图3)。在文化规制实践中,这显然是十分特殊的罕见状态。

图1文化规制的物理边界大于心理边界

图2文化规制的物理边界小于心理边界

图3文化规制的物理边界等于心理边界
如果图1、图2和图3中的心理边界是指被规制者的心理边界。第一种情况是文化规制的物理边界大于被规制者的心理边界的情况(见图1)。例如,由于意识形态的禁锢和文化传统的影响等原因,被规制者并不认同文化规制的法定边界,而是根据自己的认知判定法律规定的文化自由范围偏宽。这种观念反映到文化规制实践上,就很可能是被规制者谨小慎微地主动远离自己心中的“雷池”。第二种情况是文化规制的物理边界小于被规制者的心理边界的情况(见图2)。例如,由于思想观念的解放和权利意识的觉醒等原因,被规制者并不认同文化规制的法定边界,而是根据自己的认知判定法律规定的文化自由范围偏窄。这种观念反映到文化规制实践上,就很可能是被规制者不断争取更多的文化权利。第三种情况则是文化规制的物理边界恰好等于被规制者的心理边界的情况(见图3)。这种情况也是非常特殊的罕见状态。
从文化规制实践来看,文化规制的现实边界很复杂。因为文化规制的现实边界存在于规制者的心理边界和被规制者的心理边界所共同构成的区域之中,我们称之为文化规制的边域。文化规制边域概念的提出,显然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化规制实践中的诸多问题。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文化规制的边界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生变化的。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文化规制的现实边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规制者与被规制者之间的互动与博弈。这正是文化规制边界问题的复杂性所在。当被规制者的言行可能“越界”的时候,被规制者和利害关系人会对“越界”的风险及其后果进行相应的评估,从而寻找最佳的可选项。而在诸多考量因素之中,文化规制的物理边界是相对明确的,最不确定的就是规制者的心理边界。
文化规制的心理边界显然不止一条。规制者有自己的心理边界,被规制者也有自己的心理边界。当我们同时考虑这两条心理边界时,情况就变得更为复杂了。因为在规制者与被规制者进行互动与博弈时,文化规制的现实边界可能出现六种不同情况。假如用短线状竖虚线表示规制者的心理边界,用圆点状竖虚线表示被规制者的心理边界,用斜条纹竖灰线表示文化规制的物理边界,那么,我们可以用图4至图9来表示文化规制边界的这六种情况。

图4规制者强势缓冲型文化规制边界

图5被规制者强势缓冲型文化规制边界

图6双方各距三尺式缓冲型文化规制边界

图7规制者强势对抗型文化规制边界

图8被规制者强势对抗型文化规制边界

图9双方欢喜式理想型文化规制边界
规制者强势缓冲型文化规制边界(图4)是规制者的文化规制比较严苛,因此,被规制者享受的文化自由小于其应该享受的法定文化自由,但由于被规制者泰然处之,规制者与被规制者之间存在缓冲区域,不存在直接冲突的情况。被规制者强势缓冲型文化规制边界(图5)是规制者的文化规制比较宽松,因此,被规制者享受的文化自由大于其应该享受的法定文化自由,但规制者并不在乎,规制者与被规制者之间存在缓冲区域,不存在直接冲突的情况。双方各距三尺式缓冲型文化规制边界(图6)是规制者认定的文化自由范围和被规制者认定的文化自由范围都小于法律规定的文化自由范围,规制者与被规制者之间存在缓冲区域,不存在直接冲突的情况。规制者强势对抗型文化规制边界(图7)是规制者通过对被规制者的压制,剥夺了被规制者拥有的一部分法定文化自由,规制者与被规制者之间缺乏缓冲区域,存在紧张和对抗的情况。被规制者强势对抗型文化规制边界(图8)是被规制者通过与规制者的对抗,争取到了超出法定文化规制范围的更多的文化自由,规制者与被规制者之间缺乏缓冲区域,存在紧张和对抗的情况。双方欢喜式理想型文化规制边界(图9)是规制者的心理边界、被规制者的心理边界与文化规制的法定边界正好重合的特殊状态。在这种特殊状态下的文化规制边界就是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由此可见,规制者强势缓冲型文化规制边界、被规制者强势缓冲型文化规制边界和双方各距三尺式缓冲型文化规制边界都属于边域型文化规制边界,规制者强势对抗型文化规制边界、被规制者强势对抗型文化规制边界和双方欢喜式理想型文化规制边界则属于界线型文化规制边界。从某种意义上讲,界线型文化规制边界可以说是边域型文化规制边界的特殊情况。
四、怎样规制:文化规制的理念与原则
文化规制应该遵循三种基本理念:分界理念(解决规制边界问题)、分类理念(解决规制类别问题)、分级理念(解决规制程度问题)。
一是分界理念。对于文化规制的边界而言,有两大至关重要的原则:第一,边界意识原则,文化规制者必须树立文化规制的边界意识,严格区分公共文化空间与私人文化空间,不侵犯个人的私人文化空间,尊重和保护个人的文化私生活。第二,可预期性原则,文化规制边域的存在导致了文化规制的不确定性。规制者应该尽量减少这种不确定性,避免“选择性规制”,增强被规制者对规制结果的可预期性。
二是分类理念。文化规制涵盖面广,涉及的客体和内容,虽然有共性,也各具特色。例如,同样是出于文化冲突和宗教问题而实施的文化规制,中国清政府的禁教闭关政策就是典型的“一刀切”式规制,日本德川幕府的洋书解禁政策则是典型的“分类管”式规制。这两种理念各异的文化规制显然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了中日两国的近代化进程。事实上,文化规制最忌简单地“一刀切”,更不能鲁莽地“切一刀”,而必须根据文化规制客体和文化规制内容的不同特点,因情制宜地进行分类处理。
三是分级理念。文化规制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涵盖面广,而且体现在现实性强,涉及的文化规制相对方、客体和内容都很复杂。文化规制分级理念的最重要理由,是因为文化本身具有多样性的面貌。无论是在文化共同体之间,还是在文化共同体内部,都存在不小的文化差异和个体偏好。因此,文化产品与服务很难实现老少咸宜或皆大欢喜的要求。只有根据文化规制的相对方、客体和内容的特点进行分级,确定相应的规制等级,而不是简单查禁了事,才能真正实现被规制者的文化生活自由权和文化成果接近权。
在此基础上,文化规制应该遵循五大基本原则:透明性原则、独立性原则、合法性原则、问责性原则、适度性原则。
一是透明性原则。文化规制的透明性原则,是指文化规制信息的公开化和透明化。被规制者和规制的利害关系人有权获得同自己利益相关的文化规制信息。文化规制的透明性原则要求文化规制者及时公布文化规制信息,以便使被规制者和规制的利害关系人能够有效和充分地通过文化规制的对话机制和评估机制参与文化规制过程,通过文化规制的监察机制和纠错机制实施监督和纠正错误。文化规制的透明程度越高,文化善制的程度也就越高。
二是独立性原则。文化规制的独立性原则,是指文化规制者的自主性、公正性和客观性。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要朝打破管办不分、政资不分、政企不分、政社不分、事企不分和条块分割局面的方向前进。然而,由于文化规制者本身的意识形态偏好、规制制度环境、父爱主义惯性和经济利益瓜葛等原因,使得文化规制者的独立性和公信力较差。因为规制者与被规制者之间的渊源和关系不同,这就导致了规制者具有明显的“选择性规制”倾向。例如,某些“有背景”的被规制者就因为有规制者的“撑腰”而合法地“搓揉”竞争对手。
三是合法性原则。文化规制的合法性原则包括三方面内容:合法律性、合道德性、合利益性。相比之下,文化规制的合法律性最容易实现,但在消解文化规制合法性危机方面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文化规制的合法律性与合道德性是共同建立在文化规制的合利益性基础之上的。规制者与被规制者应该通过沟通,建立认同,从而尽可能在合利益性的基础上实现合道德性与合法律性的最佳结合。只有这样的文化规制,才是真正具有合法性的文化规制。
四是问责性原则。文化规制的问责性原则是指文化规制者的责任性和回应性。前者意味着规制者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假如规制者未能履行或者不适当地履行了文化规制职能,就是失职和缺乏责任性的表现。后者意味着规制者必须及时而有效地对被规制者和规制的利害关系人的要求作出反应。不允许无故拖延,更不能无有下文。在条件成熟时,还应该主动和定期向被规制者和规制的利害关系人征询意见、宣讲政策和解答问题。
五是适度性原则。文化规制的适度性原则是指文化规制者要掌握好分寸,主要是防止“过头”,当然也要避免“不及”。从古今中外的文化规制经验来看,当文化规制“走极端”,无论极松,还是甚严,都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文化规制缺失可能导致文化污染严重和文化暴力盛行,而文化规制过严则可能致使人们的文化生活压抑和文化免疫力低下。尤其是当一腔一调、一诗一文、一戏一曲都受到严格限制时,文化生态虽然貌似纯之又纯,但文化的凋敝已经拉开了帷幕。
五、结语:多方参与并设置缓冲消化期
在文化规制实践中,被规制者所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政策突变风险。文化规制政策的突然出台和立即执行往往会直接影响到文化产品的生产计划和市场销售,从而直接扰乱和冲击相关文化企业的战略决策和经营管理。例如,对于那些由团队合作完成并已公开上市的文化产品,由于个别主创人员的个人原因就被彻底否定。这种不可预期的文化规制政策突变,不仅造成了文化企业家和文化产业投资者的集体性焦虑,而且对文化企业乃至整个行业都产生了难以预料的突发性冲击和灾难性后果,非常不利于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的构建和完善。
事实上,无论文化规制政策的设计,还是文化规制内容的调整,都必须基于两个前提:一是文化规制政策的出台需要经过利益相关者的多方共同参与,切实保证文化规制政策过程的透明性、合法性、可问责性;二是文化规制政策的执行需要设置适当的“缓冲期”,让各方充分准备,积极应对,减少损失。否则,很容易产生文化规制的反向作用和负面影响。
总之,文化规制者应该树立边界意识,增强被规制者对规制结果的可预期性,减少文化规制政策的不确定性。文化规制者最好能够通过设置文化规制政策执行的“缓冲期”,给被规制者提供一定时间的政策“消化期”,尽可能减少因文化规制政策的突然调整所带来的政策性风险和系统性冲击。
完

(作者简介:马健,博士,西南文化产业智库执行主任兼首席专家,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说明:本文根据作者的博士论文《论文化规制——基于中外文化管理经验的研究》(已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改写和补充,特此说明。参考文献略。
来源:《艺术管理》2020年第1期(季刊)第5-13页。经作者授权转载。
关键字:边界,媒介,心理,自己的,研究,情况,文化规制内容标签: 边界 媒介 心理 自己的 研究 情况 文化规制

献给世界,你的真心,以致来世,以致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