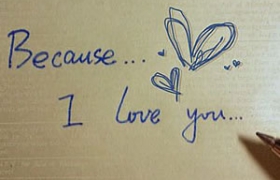历史的转折点
——现实主义转型的契机
易英
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图像学的模式》,区别了帕诺夫斯基的图像学和贡布里希的图像学。关于这个问题,文化历史学家彼得·伯克说得很清楚,“帕诺夫斯基如果不是以敌视至少也是以无视艺术的社会史而闻名。他的研究目标尽管是想找出画像的‘特有’的意义,但从来不提出以下这样的问题:这个意义是对什么人而言的?”[1] “图像学家认为图像表达了‘时代精神’。这个观点所带来的危险多次被批评者所指出,尤其是恩斯特·贡布里希在批判阿诺德·豪泽尔、约翰·赫伊津哈和欧文·帕诺夫斯基时所指出的:主张特定时代的文化是同质的是不明智的。” [2]
一般认为图像学是关于艺术作品的题材与内容的研究,解读隐藏在作品内部的意义。在图像学看来,任何艺术作品都不是自明的,只有经过对图像本身的题材与内容的分析和解释,才能知道其真正的意义。帕诺夫斯基把图像学的解释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前图像志描述,对图像的内容进行基本的识别。前图像志描述不仅有对基本事实的识别,也包括构成图像的基本条件,即是用什么样的材料和怎样的形式构成图像。第二个层次是图像志分析,对事实的具体证明,搞清楚题材的所指,故事的内容、具体的时代和环境、人物的身份,以及图像的创作时间、风格流派,等等。比如,在第一个层次,我们看到一个战争的场面,在不知道任何背景和历史知识的条件下,我们只看出是一群人在和另一群人打仗。在第二个层次,就要搞清楚这是什么战争,是奥斯特里茨战役还是滑铁卢战役。画家在什么条件下画的,是用什么手法画的,古典主义、现实主义还是象征主义。第三个层次,也是最高级的层次,是图像学的解释。历史学家把图像放入一个广阔而复杂的文化系统对作品进行考察,揭示出一个图像所隐藏的民族、文化、阶级、宗教和哲学的基本倾向的根本原则。正是这些构成图像的意义。帕洛夫斯基在解释提香的《天上的爱和人间的爱》时,编织了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背景,不只是哲学解释了图像,图像也证明了哲学。艺术与文化共生,图像的意义纳入一个看似合理的逻辑框架。问题在于艺术家不是哲学家,甚至艺术家可能根本就不关心哲学,艺术家怎么会按照一个哲学的命题来生产图像。而且,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并没有根本摆脱工匠的身份,和人文主义者相比,艺术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别说研究哲学,就是一般的哲学理论他们也可能看不懂。关于这个问题,有两个解决的途径。一个是艺术家并非直接根据哲学来创作,而是在现成的艺术样式上注入新的观念,如同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是从中世纪逐步演变而来的一样,特定的艺术样式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增加新的内容。艺术家实际上是从前在的图像和某种规定的样式中来创造新的图像。例如,柏拉图的《会饮篇》讨论过两个阿芙罗底德,同为女神,一个代表神圣,一个代表世俗。经过新柏拉图主义者菲奇诺的解释,她们又分别代表了宇宙智慧与灵魂,世俗与欲望。在文艺复兴的饮宴题材的绘画中,女性形象总是包含着这样的意思。通过饮宴题材的形象可以解释提香的《天上的爱与人间的爱》,剩下的问题是怎么知道提香根据哪幅饮宴画来创作的。帕诺夫斯基认为在某个特定的场合曾有过饮宴的壁画,提香经常出入这个场合,肯定看过并了解这幅画。提香的工作不是诠释原画中的哲学思想,而是把原画的视觉主题明确化和审美化。第二个不是这种文化的推论和假定,而是以具体的事实为依据,证明艺术家是根据一个人文主义的方案来创作的。这也涉及图像学的另一个概念,图像的解释就是弄清楚画家所要表达的意思。这个意思可以是画家自己的,也可以是别人通过画家来表达的。帕诺夫斯基不能证明艺术家是怎样根据人文主义者的方案来创作的,贡布里希则用具体的事实来说明波提切利的《春》是怎样从一个方案中产生的。一个由委托人、哲学家和经纪人组成的班子,制定一个人文主义的方案,艺术家是这个方案的执行者,将人文主义的思想转换为视觉表达,而且具体的表达方式也包括在方案之中。
巴克桑达尔将他的艺术史方法称为艺术社会史,他说:“一幅15世纪的绘画系某种社会关系的积淀。一方为绘画作品的画家或至少是此画的监制者;另一方为约请画家作画、提供资金、确定其用途者。双方均受约于某些制度和惯例——商业的、宗教的、知觉的,从最广义上说,社会,这些不同于我们的制度和惯例影响着该时代绘画的总体形式。”[3] 贡布里希研究了一个视觉图像是如何在社会条件下产生的,艺术家的思想来源是什么。巴克桑达尔进一步强化了社会的作用,艺术家及其作品本身都是社会的产物,艺术家的创造性功能也是置于社会关系之中,一定的社会“制度与惯例影响着该时代绘画的总体形式。”巴克桑达尔特别指出了艺术家的形式是怎样受制于特定时代的视觉环境,正是视觉环境决定艺术家的形式选择。在形式主义看来,艺术史就是风格演变的历史,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特定的风格,社会与历史的条件可能影响和延缓某种风格的发生,但新的风格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新的风格都是通过伟大的艺术家体现出来的。图像学不关注风格与形式,在内容的阐释上没有大师与平庸的区别。图像学不能解释艺术的发展,不能解释艺术形式与艺术家的个人创造之间的关系,社会学是对这一点的弥补。但是,在社会的制度与惯例影响着时代绘画的总体形式的时候,艺术家的个人作用是什么,艺术家的主动创造与社会影响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显然不是单纯的图像学和社会学能够作出解释的。
一种风格的产生刚开始是不为人知的,因为它淹没在已有的风格中。在与传统的风格和正在发生的其他风格的竞争中,新的风格发展壮大,独领风骚,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李格尔的《风格论》论述了一种风格产生的过程,新风格首先潜藏在传统之中,在众多的样式中,出现某种变异的图案和纹样,往往预示着新风格的来临。在艺术创作中也是如此,“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历史,而是在直接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 每个时代都有其时代的艺术,每个时代的艺术都具有不同于其他时代的艺术特征,李格尔说,作为个别的艺术家可能会失败,但一个时代的艺术意志必定会实现。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往往是新风格的创造者,同样,衡量一个艺术家是否伟大,就在于是否创造了新的风格。一个艺术史的阶段也是以某种独特的风格为代表,其起源与发生,成熟与鼎盛,没落与衰败;然后,新的风格诞生,新的时期开始。风格学以风格的发生和演变为对象,通过形式的分析与类比,在历史的尽头寻找形式的证据,从而开始风格史或形式史的演进。一种新风格怎样产生,一种新形式怎样创造,有无特定的语境,有无特定的动机或契机,似乎都不是风格史家的工作。李格尔在谈到风格起源时说过,“社会和宗教的现象是与艺术相互平行的现象,而不是影响艺术起源与发展的潜在原因。而这些平行现象的背后,是不可捉摸的世界观,或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在起着支配作用。”[5]帕诺夫斯基在解释李格尔的“艺术意志”时也说过同样的意思,文化的整体运行支配个别的艺术事实。但是,对艺术创作而言,不论是风格的演变还是形式的变化,总是通过具体的艺术家来实现的,如李格尔所说,世界观、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既影响着社会和宗教,也影响着艺术,但不是影响艺术起源和发展的潜在原因,这个意思是说不能把风格的起源和发展与它们直接联系起来。事实上,新风格的产生是有原因的,一种风格替代另一种风格,似乎是历史的必然,但历史并不知道,为什么一定是这种风格来替代,而不是另一种。即使是一种风格降临在艺术家身上,艺术家成为新风格的承载者和实现者,那么这种降临也必定是艺术之外的原因。也就是说,艺术家不可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
19世纪中期是欧洲艺术史上的一个转折时期,一方面是学院主义的鼎盛时期,另一方面是现实主义的出现,预示了学院主义的终结和现代主义的发生。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有米勒和库尔贝,但直接与学院主义对抗并改写了古典与学院风格的则是库尔贝。波德莱尔在《一八四六年的沙龙:关于现代生活的英雄主义》一文中说:“裸体画,艺术家们的宠儿,成功不可缺少的部分,今天一如与古代一样频繁和必要:在床上、在浴池或在解剖室。绘画的主题和来源同样丰富多变,只是有了一个新元素,即现代美。”[6] 现代生活的英雄和现代美都是有所指的,它区别于传统,强调现代生活的人物及其所体现出来的表现他们的形式。英雄有着双层性,既是古代神话和宗教中的英雄人物,也是古典艺术中表现英雄的艺术样式。这种样式形成于文艺复兴,在19世纪中期的学院派艺术中达到顶峰。在1862年的沙龙,获大奖的是亚历山德拉·卡巴莱(Alexandre Cabanel)的《维纳斯的诞生》,这个在海水中诞生的女神完全是学院主义的产物,延续了古典传统的裸体表现。与此同时,爱德华·马奈的《奥林比亚》和《草地上的午餐》也画于这个时候,这可能就是波德莱尔说的床上的裸体。不过,波德莱尔说这话的时候,马奈的作品还没出来,另一个与他有来往的现实主义画家是居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在库尔贝的著名作品《画室》中,就有波德莱尔的影子,库尔贝认为波德莱尔是他的思想来源之一。库尔贝这时正致力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波德莱尔把它称为自然主义。波德莱尔说:“对我们来说,自然主义画家和自然主义诗人一样,几乎是妖魔。他们唯一的鉴赏标准是‘真’(当‘真’被用得恰到好处的时,也是十分崇高的)。”[7] 波德莱尔是很敏感的,他意识到了新风格的来临,这种风格就是如实地反映生活,不仅在题材上,更重要的是在形式上。自然主义的形式就是自然的本来面目,有能力的画家不会按照自然的本来面目来作画,他们总是要把自然纳入美的范畴,使自然不成其为自然,而是在某种标准下的美的提升。1861年,在对“淫荡画”的创作者的指控中,帝国检查官琴德瑞说,艺术家拒绝理想的美是基于美学的堕落,以此解释淫秽形象的流行:“直到最近,在绘画领域,我们看到一种所谓学院的‘现实主义’的出现,以制度的名义违背美……取代意大利和希腊的美女,一些种族不明的女人令人遗憾地在塞纳河两岸留下了标记。”琴德瑞的指控与库尔贝的画脱不了干系,早在十年前库尔贝画出了“淫荡”的裸女,引起过一片指责。不过,库尔贝的追求不在“淫荡”,而在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表现。
现实主义无疑以库尔贝为代表,这种新风格是从哪儿来的,他敢于抛弃学院派的造型规则,直接描绘真实的形象,不加任何美的修饰。1849年沙龙库尔贝展出了《奥尔南的餐后》,这件作品标志着库尔贝在艺术上的成熟,此后他不再那种感伤性的题材,而致力于真实的单纯的农民形象,而且还是要用纪念碑的风格来画这些农民,对库尔贝的指责和讽刺也从这时候开始,认为他画的形象“粗俗”、“丑陋”。库尔贝没有很好的学院派的基础,他早期在家乡奥尔南的一所美术学校受过简单的训练。他的父亲不同意他学习艺术,还是要他学习法律,将来好当律师。他到巴黎本来也是为了学法律,但他还是迷恋艺术。他没有去美术学院学习,而是自己到博物馆学习,他认为直接向老大师学习,更能接近艺术的真谛。库尔贝在技术上很有天赋,他无师自通,没有受过严格的古典训练,主要靠临摩古典绘画,却也具有了严谨的造型能力。从1840年代中期以来,这位年轻艺术家对老大师十分熟悉,虽然他一再表明他是自学的。库尔贝在那时是卢浮宫最勤勉的访问者;年轻女人动人的睡姿,丰满的身体,侧卧的方式,与它煽起的欲望无关,其深度直接出自柯罗乔的《维纳斯》。虽然他从老大师那儿学习的是古典美,但他的创作却是自己的一套。他不画古典题材,他画的都是现实生活,现实主义由此而来。他的题材大多来自他的家乡奥尔南的乡村生活,如果是巴黎的题材,也是画的下层人物的形象。对于学院主义的憎恨很可能出自他对巴黎人的不满,尽管他的家族在地方上不是下层的劳动人民,他父亲是一个商人兼地主,他的经济条件足以支撑他的艺术活动,但他在巴黎仍被视为乡巴佬。他也干脆回到奥尔南作画,那儿不仅有他熟悉的生活,也有学院主义无法表现的形象。
1849年,他的《奥尔南的餐后》在沙龙展出,那种乡土味十足的室内场景却使他获了奖,库尔贝为他高超的技巧而骄傲,他倒不认为乡土题材比技巧更重要。但是评论并不接受他的题材,有一篇评论尖刻地说:“没有谁能够用这样高超的技巧来画阴沟里的东西。”高超的技巧是指库尔贝的造型能力,他确实发展出一套自己的画法,这种画法很难为传统的人士所接受。《奥尔南的餐后》画于1849年,早于库尔贝的其他现实主义作品,被认为是库尔贝的第一个现实主义宣言,以其大胆和不羁挑战传统的造型。“阴沟里的东西”关键在于这些东西散发出来的阴沟的味道,“阴沟”其实是西方绘画的传统题材,从宗教到神话,绘画的故事很多是在田园和乡土展开,或者在市井街陌,如拉斐尔的田园里的圣母,卡拉瓦乔的酒馆里的使徒,但这些人物都是理想化的,造型都是希腊式的(19世纪的法国称为“意大利式的”)。19世纪中期,在法国和英国,画劳动题材和社会下层题材的画家不少,这些画家可能接受了现实主义的影响,可能具有社会主义的思想,但他们画出来的并非真正的现实主义,像是学院派的演员穿上农民的服装在舞台上的表演。如我们比较熟悉的法国画家莱昂米特的《收获的报酬》,表现的是农民题材,也对社会的不公进行了批判,然而整个画面仍然是古典式的,向心式的构图,犹如舞台剧的结构;人物造型如同希腊雕塑,甚至形象都像古罗马的将军。林达·诺克林说:“在观念或政治上的‘进步’或‘跟得上时代’绝不意味在作画时也能有相类似的进步表现。这也就是1848年二月革命的实际现实往往表现在一些画风低调、平和的画作上的原因,……”[8]再看库尔贝的《奥尔南的餐后》,非常平实的场面,现实生活的真实记录,没有任何激进思想的设定,就是画他的“如我所见”。人物的布局随意而散乱,只是一个偶然的瞬间,中心的人物背对着画面,也是偶然的回头,人物的动作完全是生活的原样。这种随意性的构图和偶然性的动作,都不是学院派的绘画能做到的,即使是有意地追求普通生活场面的表现。
这样的处理很可能是参考了照片,消解理想化的造型,捕捉随意的生活场面,都是照片可以做到的。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库尔贝都是在他的家乡奥尔南作画,最有名的作品当然是《奥尔南的葬礼》。研究库尔贝的学者德斯普莱斯(Desplaces)针对《奥尔南的葬礼》的表现手法说过:“愿意的话,你可以说是想象,艺术家根据头脑中的想象画出模糊的乡村葬礼,给它以纪念碑式的绘画比例。这只是一种幻想,给日常生活的场面以纪念碑式的比例,似乎不是库尔贝的发明,但他完全意识到,通过大幅的着色的银版(达盖尔)照片来复制最粗俗的农民形象。”[9] 这并不是说库尔贝直接用照片来复制现实的场景,而是说库尔贝画的农民像照片那样逼真和粗俗。实际上,在这一时期,库尔贝对摄影照片确实也很感兴趣。他的一些作品直接参照了照片,照片为他提供了自然主义;同时照片对他也意味着一种艺术观念,不仅仅是表现手段。针对19世纪摄影和绘画的关系,波德莱尔说:“对我们来说,自然主义画家和自然主义诗人一样,几乎是妖魔。他们唯一的鉴赏标准是‘真’(当‘真’被用得恰到好处时,也是十分崇高的)。”“在这值得悲哀的时期,产生了一种新型工业,它对巩固这种信仰中的愚笨和毁坏任何可能存在于法国人头脑中的神圣的东西都丝毫没有贡献。达盖尔是他的救世主。”“现在,忠实的人对他自己说:‘既然摄影能保证我们追求的惟妙惟肖,那么,摄影和艺术就是一回事了’。”[10] 摄影的产生催生了自然主义(现实主义),也引起了学院主义的敌视。学院主义不是反对摄影本身,而是反对绘画像摄影那样,毫无美感地复制粗俗的自然。库尔贝需要的正是这种效果,既找到一种方式达到自然真实的效果,又满足了他反对学院规则的需要。摄影如实地反映真实,它消解了绘画对现实的美化。它再现了人体的真实比例,为准确地造型提供了一条捷径,学院主义苦苦追求的逼真再现,摄影似乎毫不费力地达到了。波德莱尔站在前卫的立场,讽刺了学院主义面对摄影的恐慌,也意识到了这种新媒介可能对艺术带来根本性的变化。
库尔贝对摄影的态度是矛盾的,他目睹了直接复制照片的绘画在沙龙的失败,也尝试了用摄影代替写生,让模特儿摆出学院的动作,通过摄影的记录,再搬上画面,《筛谷者》可能就是这样画的,两个模特儿都是他的妺妺。后者的画法,仍然没有摆脱学院的局限,尽管是画的劳动题材。1853年,库尔贝的朋友,画廊老板阿尔弗雷德·布洛亚(Alfred Bruyas)给在奥尔南的库尔贝寄了四张照片,都是布洛亚画廊藏画的复制,一张德拉克洛瓦的肖像草图,一幅肖像画,另外两幅学院派画家的作品。在一张照片后面布洛亚写了几句话:“亲爱的库尔贝,好好看看我给你这几张照片。这是现代绘画的真实之歌。既要按照绘画又要按照摄影产生的真实的版画来看待它们。”[11] 早期的摄影还不是采用底片洗印的照片,盖达尔银版摄影只能产生一张照片,照片的复制是采用版画的技术。因此,早期的摄影有很多版画家参与,版画家更了解艺术家对摄影的需要。库尔贝收集了很多这种版画式的照片,有一些是直接用于创作的素材,请摄影师或版画家为他订制的,有一些是创作的参考,不见得直接用于创作,有些模特儿的照片,更像是工作的记录。一直到库尔贝创作的后期,都还在参考这些照片。大多数照片都没有保留下来,一是因为普法战争期间,他的画室遭到普鲁士士兵的洗劫,大多数照片不知去向。二是因为他的妹妹认为那些照片有伤风化,处理掉了一部分。女人体的描绘是库尔贝反对学院派的一个突破口。人体表现不仅包含了人体造型的众多规则,还有理想化的要求,官方的趣味和整个上流社会的集体认知。安格尔、卡巴拉、布格罗这些学院主义的大师,把人体艺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单纯的农民题材,似乎不能引起学院的关注,从人体入手,才真正动了学院主义的神经。在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女裸体的表现(除了早期以外,他几乎不画男裸体)成了库尔贝的武器,从现实主义、古典主义到色情描绘,从形式到内容,他从人体艺术的各个方面与学院派对抗,直到70年代初的巴黎公社才结束。在这个过程中,1852年《浴女》显然处在最重要的位置,而摄影在其中又具有最重要的作用。在后来的《画室》中,库尔贝身后的那个裸女,就是《浴女》中的模特儿,库尔贝把她画在这儿,也是要强调“她”在他的艺术生涯中的重要意义。
库尔贝 《浴女》1853年 布面油彩 227×193cm 蒙彼利埃,法布尔博物馆 1868年布吕亚捐赠
朱利叶·沃龙·德·维伦内夫(1975-1866)《自然研究,裸体第1936号“浴女”的模特》 1853年 纸质底片的盐版相片 16·5×12·3cm 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版画和摄影部
《浴女》画于1853年,1852年在他的家乡奥尔南完成了一半,其他部分在巴黎画的,周边的环境是典型的奥尔南风景,两个女人的动作仍然有学院的痕迹,似乎是先在画室摆出造型,然后再配上风景。裸体的女人刚刚沐浴完毕,着衣的女人则不知在干什么,似乎是裸体女人的陪衬。这显然不是一个现实的题材,与他其他的奥尔南题材大不一样,裸体似乎是他的目的。这件作品他是要提交给沙龙的,在动手作画之前,他就说过:“下个展览我决定除了裸体,不交别的画。”库尔贝要画出和学院派不同的裸体,还要提交给沙龙,扰乱学院主义的秩序。尽管库尔贝在女人体的动作和肉体表面的处理上顺从了沙龙的要求,但《浴女》还是被沙龙拒绝了,用德拉克洛瓦的话来说,就是“形式的粗俗”与“思想的粗俗”,那个肥硕健壮的农妇般的裸体,与学院派的维纳斯有天壤之别。
《浴女》中的两个人物是在奥尔南画的,因为在保守的奥尔南不可能找到裸体模特儿,库尔贝画中的裸体都是来自摄影的模特儿。他的妺妺后来烧掉的那些“不雅”的照片,应该就包括了这批照片。库尔贝对照片的认识还不始于《浴女》,在此之前,他就画过弗兰什-孔代风景中的女裸体,这些裸体也是来自照片。对库尔贝来说,照片是他探索新的艺术语言的工具。照片提供的古典姿势意味着他保留了他对古典大师的忠诚,另一方面又摆脱了学院主义的理想美的束缚;极其自然的照片中的女人是一个“真实的”女人。早期的摄影与绘画的关系并不是一目了然的,不是艺术家为了创作寻找真实的模特儿,再通过摄影复制到作品。最早都是由摄影师把照片拍得像古典的绘画,由此像绘画一样参加沙龙的展览。模特儿摆出古典的动作,可以作为独立的摄影作品,也可以为艺术家服务,艺术家从中寻找古典的灵感,或通过照片校正古典的动作或比例。由于照片的复制技术接近版画,很多版画家参与了摄影的活动,受过学院训练的版画家很了解古典艺术的要求,他们选择合适的模特儿,按照希腊-罗马的样式摆出古典的动作,再拍成照片,完成一件“古典艺术”的摄影作品。问题在于,很多版画家并不把这样的照片作为独立的艺术作品,而是把它作为古典艺术的样本提供给油画家用于古典造型的参照。当然,版画家的行为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但无形中导致照片的泛滥,艺术观念的“低下”。那些裸体的“古典”都是现实中“丑陋”的身体,真实的女裸体也会导致色情的联想。然而,库尔贝正是从这中间看到了“商机”,他要寻找的正是“丑陋”的身体,用以对抗学院的“理想”,而潜在的色情也是对社会规范的挑衅。丑陋总是和真实相联系,非理想的身体比例,肥硕臃肿的躯干,平庸的相貌,笨拙夸张的造型,等等,这些都毫无修饰地出现在照片中,同样也出现在库尔贝的作品中。1861年,帝国检查官琴德瑞(Gendreau)没指名地攻击库尔贝:“直到最近,在绘画领域,我们看到一种所谓学院的‘现实主义’,以制度的名义违背美……取代意大利和希腊的美女,一些种族不明的女人令人遗憾地在塞纳河两岸留下了标记。”[12]
点击图片,在新窗口显示原始尺寸
皮埃尔·安布鲁瓦兹·里什堡(1810-?1875) 《斜倚的女人体》 约 1855年 立体达盖尔版照片 8×17cm 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版画和摄影部
朱利叶·沃龙·德·维伦内夫(1975-1866)《自然研究,裸体第1906号“画室”的模特》 1854年 纸质底片的盐版相片 16×11·4cm 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版画和摄影部
朱利叶·沃龙·德·维伦内夫(1975-1866)《自然研究,裸体第1930号》 1854年 纸质底片的盐版相片 14×9·1cm 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版画和摄影部
朱利叶·沃龙·德·维伦内夫(Julien Vallon de Villenve),学院派画家,1820年代跟达维特学习绘画,1824年第一次参加沙龙展览。除油画外,他在大部分时间都是做版画。他和著名摄影家希波利特·巴亚尔(Hippolyte Bayard)关系密切,他们在40年代一起进行过改进制版的工作。沃龙为他的艺术家朋友提供照片,很多都是由演员装扮的各种形象,有老年的神父、穿各种服装的男子和东方服装的年轻女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女裸体。在沃龙使用的模特儿中,有一个模特儿年龄偏大(其他都在20岁以下),体形较胖,黑色头发;这个模特儿的照片有20张(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不同的姿势,简朴的环境,有些是全裸体,有些披着白布。1955年,美术史家让·阿德赫马首先指出了沃龙的照片与库尔贝的《浴女》和《画室》中的女裸体的相似。他说:“艺术家(沃龙)在四、五十岁之间的1835-55年发表了这些模特儿中的两个人的形象,他的版画创作已经下滑,而转向摄影。他为库尔贝的《浴女》使用真实的模特儿起了作用。”不过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明库尔贝是使用沃龙的照片,他们不是一代人,可能也不相识,作为古典艺术家的沃龙,也不在库尔贝的激进艺术的圈子里面。但有间接证据说明库尔贝使用的照片。库尔贝在给他的藏家,画廊老板阿弗雷德·布洛亚的信谈到他的《画室》的构图:“就此而言,他务必寄给我……我跟你说过的那张裸体女人的照片。她位于画中间我的椅子后面。”《画室》中库尔贝身后的那个女裸体与《浴女》中的背对画面的裸妇是同一个人。直到1873年,传记作家希尔韦斯特雷在给布洛亚的信中说:“你给我的照片上的模特儿,库尔贝在《浴女》中用过,她叫亨里特·本尼昂(Henriette Bonnion)。我见过她按照你的照片为库尔贝摆动作。”沃龙的照片和库尔贝的《浴女》虽然是用的同一个人,动作、体形都很相似,但观念表现完全不同。沃龙柔和了女人体优美的轮廓,降低了明暗对比,减弱了阴影,好像有学院人体的平滑效果。库尔贝坚决反对这种学院的表现,毫不妥协地描绘了亨里特·本尼昂的物理事实:肥大的臀部、变形的丰满和上年纪的身躯。
库尔贝达到了他的目的,尽管一些批评家对作品的技术特征表示认可,但大部分人对这幅画难掩厌恶之情。漫不经心的动作、肮脏的脚和掉落的袜子都是污秽的象征,没有道德的表现。模特儿的体格违背了学院的标准,像是有意的冒犯。最客气的批评家戈蒂埃把“她”称为“霍屯顿(原始部落)的维纳斯”。但是,一个外省的年轻收藏家以3000金法郎买下了这幅画,他就是布洛亚(沃龙的本尼昂照片也是他的收藏),作品的丑闻已传到他的家乡蒙彼利埃,画幅的尺寸也完全不适合中产家阶级家庭的布置,但他显示出和画家一样的勇气,他要确保库尔贝追求艺术真理的胜利,经济上的独立使他能摆脱官方的迫害和限制。
库尔贝的《浴女》没有选上当年的沙龙,而参加了落选沙龙,对于这个结果,库尔贝说,“要给有点惹人的屁股遮上点什么”。皇帝和皇后在开展之前来到沙龙,皇后的眼光被博纳尔的《马集市》所吸引,画中的马屁股对着外面,欧仁皇后问道,为什么它们的形状完全不同于她熟悉的那些优雅的动物。后来,她来到《浴女》面前,她用幽默的提问向皇帝表示她的迷惑:“这也是一匹佩尔什马吗?”后来的传说是,波拿巴皇帝假装用他的马鞭抽打浴女的臀部。[13]
[1] 彼得·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P49。
[2] 同上,P51。
[3] Michael Baxandall, Painting and Experience in 15th century Italy, first published (197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3.
[4]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5] 李格尔,《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陈平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P37。
[6] 《现代艺术和现代主义》,弗兰西斯·弗兰契娜、查尔斯·哈里森编,张坚、王晓文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P23。
[7] 同上,P25。
[8]《现代生活的英雄》,琳达·诺克林,刁筱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P135。
[9] Desplaces, in L’Union 29. From Gustave Courbet,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2008, P36.
[10] 《现代艺术和现代主义》,弗兰西斯·弗兰契娜、查尔斯·哈里森编,张坚、王晓文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P26。
[11] Dominique de Font-Reaulx, Realism and Ambiguity in the Paintings of Gustave Courbet. 原注:这4幅印刷品现藏巴黎国家艺术史学院图书馆,库尔贝在1854年1月给布洛亚的信中说:“至于我,很高兴收到你的照片,我正给它们衬个底子。”From Gustave Courbet,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2008, P38.
[12] Desplaces, in L’Union 29. From Gustave Courbet,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2008, P343.
[13] 以上均参阅:The Nude: Tradition Transgressed. From Gustave Courbet,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2008, P338-387.
关键字:艺术家,艺术,图像,风格,都是,绘画,内容标签: 艺术家 艺术 图像 风格 都是 绘画

献给世界,你的真心,以致来世,以致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