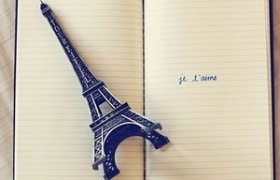西方现代美学和批评的一个主题,便是对作品风格——根据夏皮罗的定义,亦即形式要素、形式关系及形式品质——的知觉和鉴赏。正如我们在前文引用过的夏皮罗的名言所说,在推翻了题材和主题的等级制并将艺术价值从题材和主题本身当中剥离以后,艺术的剩余价值基本上落实到风格之中,也就是艺术家所调用的形式要素、关系及其品质之中。在诸多要素、关系与品质中,对作品笔触和线条风格的认知和辨析,成了艺术史家最基本的职责之一。这正好属于夏皮罗这类艺术史家的擅胜之地。在这本选集里,夏皮罗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个案,可以方便我们抵达这一最了不起的艺术史和美学王国。这一个案便是《批评家欧仁•弗罗芒坦》。

欧仁·弗罗芒坦 《猎羚羊》 油画 27×36cm
在此文一个谈及弗罗芒坦的历史知识的语境里,夏皮罗提到了黑格尔,并认为在对荷兰绘画,特别是荷兰绘画与政治环境的研究中,黑格尔的思想首屈一指:“在此书里,荷兰艺术的社会基础[许久以前曾由黑格尔作过无比聪明的阐述,然后又由丹纳做过不那么透彻的解释],不仅被当作某种完全可信的东西加以呈现,而且也被当作艺术生产及其私密性质的必要条件。”[1]
那么,黑格尔是如何研究荷兰绘画的呢?他首先指出了荷兰绘画之于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变革:
谈到这一点,我们要用以下的方式来说明荷兰绘画的转变的理由,即从教堂和宗教虔诚的观点和形象塑造的方式,转变到单纯的世俗生活以及自然界的事物和一些特殊具体的现象,例如正当的欢乐的安静的但是狭窄的家庭生活,乃至民族的喜庆,宴会和列队游行,农村舞蹈,教堂节日的娱乐和游戏之类。[2]
具体地说,这些理由包括:荷兰的宗教改革、政治独立,以及日耳曼人的性情气质(按:荷兰属于北欧日尔曼民族)。在交代了荷兰所发生的变革的原因后,黑格尔提供了对荷兰绘画的一般特征的描绘:
这个聪明的具有艺术资禀的民族也要在绘画中欣赏这种强旺而正直的安逸的殷实生活,要在一切可能的情境里从图画中再度享受他们的城市,房屋和家庭器皿的清洁,家庭生活的安康,妻子和儿女的漂亮装饰,城市政治宴会和富丽辉煌的排场,海员的英勇以及他们对本国的商业在全球各海洋上行驶的船舰的声誉所感到的欣慰。荷兰画师们也正是把这种对正当的愉快生活的审美感带到对自然题材的描绘里去,他们在一切绘画作品里,都能把构思的自由的真实,以看来似是微不足道的只在瞬间出现的事物的爱好,敞开眼界的新鲜感以及对最孤立绝缘和最有局限性的事物的聚精会神这些特点和艺术布局方面的最高度的自由,对次要因素的最精微的敏感及创作施工方面的周密审慎结合在一起。[3]
尽管这一描绘建立在他对荷兰绘画与社会背景的独特见解之上,他对荷兰绘画一般特征(特别是其题材的特征)的描绘也颇具新意。假如读者对黑格尔的主要意图并不是艺术史的叙述而是对美学(或曰艺术哲学)的论述这一点抱有同情的理解,那么,黑格尔确实说出了一些东西。但是,他说得过于笼统、过于粗疏,也过于抽象了。其中没有艺术家,也没有具体作品。在他提到荷兰绘画的本来就很少的篇幅里,似乎只提到过凡·艾克兄弟,却没有提及他俩的任何一幅画。而黑格尔最具体的观点尽管已经点到类似风格或形式的问题(“形成诗的基本特征的东西”),也提到了表现方式和“艺术施工”,但也只能点到为止:
在这里形成诗的基本特征的东西就是大多数荷兰画家所表现的这种对人的内在本质和人的生动具体的外在形状和表现方式的认识,这种毫无拘束的快活心情和艺术性的自由,这种想象方面的新鲜爽朗和这种艺术施工方面的既稳妥而又大胆的手腕。[4]
这也难怪为黑格尔的荷兰绘画研究做注的朱光潜先生,特别论及黑格尔注意到了荷兰绘画题材上的突破,但对于具体内容、表现手法,特别是风格,除了“现实主义”这样宽泛的用词,则语焉不详:“论荷兰画这一节是值得特别注意的。过去艺术史家和批评家们都特别推尊意大利画,意大利画艺术造诣固然很高,但在题材方面局限在宗教领域,在创作风格方面仍没有摆脱古典理想的束缚;荷兰画开始侧重现实生活,真正反映了资本主义时代新兴市民的精神,可以说是在绘画中开创了现实主义风气。黑格尔在《美学》中再三给荷兰画以很高的评价,在这方面他是开风气之先的。”[5]
在开始写《比利时与荷兰的老大师们》这本书之前,丹纳在其《艺术哲学》里早已写下了有关佛莱德斯和荷兰绘画的一些令人目眩神迷的章节,“用辞藻繁富、思路清晰的文字,断言了种族和环境对这些艺术的影响”。但是,在读过丹纳及其他人的作品以后,弗罗芒坦得出结论认为,“在某个层面上,一切都还有待于研究;关于佛兰德斯和荷兰的老大师,世上还没有一本真正重要的书已经出版,至少还没有足以与他本人对这些艺术家个性的洞察相比拟的书”[6]。

《艺术哲学》[法]丹纳 著 傅雷 译

伊波利特·阿道尔夫·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法国十九世纪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史学家,历史文化学派的奠基者和领袖人物,被称为“批评家心目中的拿破仑”。
我早年属于耽读傅译丹纳《艺术哲学》的那类心醉神迷的读者。不过,回过头去看,我不得不说,丹纳对比方说荷兰绘画的种族、民族和时代、环境说得越多,我就越是觉得他对荷兰绘画本身说得越少。对于前者,他说了又说,例如在关于伦勃朗的那个著名小节里:
从1600年起,一切都变了,在绘画和别的方面一样,充沛的精力使民族的本能占据优势。裸体是放弃了;理想的人体,过野外生活的鲜剥活跳的人,四肢和姿势的美妙的对峙,大幅的寓意画和神话题材,都不合日耳曼口味。并且,控制思想的加尔文主义把这些作品排斥在教堂之外。在这个俭省、严肃、爱劳动的民族中间,根本没有王侯的宴会行乐,享用奢华的生活,不像在别的地方的宫殿中,在银器、号衣、精美的家具之间,需要肉感的和异教意味的图画。[7]
关于伦勃朗,他甚至指出了其视觉的构成,而这通常是20世纪的人们才会注意到的事实;在这方面,他可谓大大超越了黑格尔:
伦勃朗是收藏家,性情孤僻,畸形的才具发展的结果,使他和我们的巴尔扎克一样成为魔术家和充满幻觉的人,在一个自己创造而别人无从问津的天地中过生活。他的视觉的尖锐与精微,高出一切画家之上,所以他懂得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对眼睛来说,有形的物体主要是一块块的斑点;最简单的颜色也复杂万分;眼睛的感觉得之于构成色彩的元素,也有赖于色彩周围的事物;我们看到的东西只是受别的斑点影响的一个斑点;因此一幅画的主体是有颜色的,颤动的,重叠交错的气氛,形成浸在气氛中像海中的鱼一样。[8]
但是,没有关于伦勃朗的任何一幅画的研究,也没有关于伦勃朗个人风格发展的任何叙述。因此,这很让人怀疑傅雷先生的断言:“他的《艺术哲学》同时就是一部艺术史。”[9] 特别是考虑到丹纳的如下自白:“的确,艺术家创作的时候只凭个人的幻想,群众赞许的时候也只是一时的兴趣;艺术家的创造和群众的同情都是自发的、自由的,表面上和一阵风一样变化莫测。虽然如此,艺术的制作与欣赏也像风一样有许多确切的条件和固定的规律,揭露这些条件和规律应当是有益的。”[10]
也就是说,丹纳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揭露艺术制作与欣赏……确切的条件和固定的规律”,而不是提供一种较充分的艺术史叙述。我以为,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艺术史作为一个学科尚不发达,不得不借重于美学和艺术哲学;另一方面,也是人类认识事物的普遍规律所致:始则粗疏阔略,终而精密沉深。丹纳的艺术哲学(或傅雷称之为“艺术史”),比之黑格尔已大大具体化;但较之以弗罗芒坦和夏皮罗为代表的那个艺术史和批评传统,则仍然处于质朴简陋的阶段。
不幸的是,我国的艺术史教育大体上还停留在黑格尔和丹纳的水平上。尤其是体制内的科教书,依旧满足于时代背景(特别是由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经济基础以及时代的阶级状况)、艺术家生平(简单的传记材料)、代表作简介(对若干代表性艺术品充满陈词滥调的描述)这样的三段论模式中。换言之,我们的教科书除了关于时代背景和艺术家平生的简单介绍外,并没有关于艺术风格特征及其演化的可靠陈述。这也部分解释了体制外的教科书——例如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至今仍然是读者(甚至包括所谓的专业读者、美术学院的教授们)争相阅读的书目的原因。
这样,我们或许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弗罗芒坦会感到,在他之前,还没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荷兰(及比利时)的绘画研究。弗罗芒坦何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答案正在于他的画家身份,以及批评家的眼光。在他之前,尽管不乏零星的闪光,但总的来说,黑格尔、丹纳们满足于艺术与时代、种族的笼统陈述,却疏于对艺术品的物质质地、材料肌理和画面质感,特别是艺术风格的鉴别与观照。这些正好是弗罗芒坦的用武之地。或许正因为这一原因,夏皮罗选择了弗罗芒坦。
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个了不起的现代艺术史和艺术批评的传统:始于李格尔对风格的两极性概念(视觉-触觉)理论,然后是希尔德布兰德的形式美学、莫雷利对艺术家个人风格的鉴定、贝伦森强调的视觉艺术的触觉价值,直到罗杰·弗莱的形式主义美学。特别是在罗杰·弗莱那里,这一传统趋于完满。弗莱关于形式而非主题才是绘画最重要的表达元素的理论,为现代主义-形式主义理论完成了奠基。弗莱在“形式作为表达元素”的理论,特别是关于笔触和线条等形式要素的研究中,寻幽探胜,深入了极其精微的畛域。
在《线条之为现代艺术中的表现手段》一文中,弗莱对线条有着极其深刻的论证。他在文中提出有两种线条,一种是以很快的速度画下,自由流畅,快速地勾勒物象;另一种严谨缓慢,似乎被安排进了某种图式当中。弗莱称第一种是书法式的(calligraphic)线条,另一种是结构式的(structural)线条。
弗莱对书法式线条的界定是,它“画得十分迅速”,“几乎拥有某种夸张的细腻与感性” [11]。他以现代绘画大师马蒂斯的线条为例,认为马蒂斯的线条具有一种令人震颤的生命强度,有其大胆而令人痴迷的富有韵律的特点;那种可以来自观看马蒂斯素描的独特的狂喜情绪,就仿佛来自观看某些高难度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平衡表演时所感到的兴奋。在对自然形式如此大胆的简化中,观众能够感到那种机械的、仅仅是程式化的东西,掩藏在背后。换言之,马蒂斯自由、流畅的挥洒,来自长期的训练,从而掩盖了其背后那种更为严格的图式。
然后,弗莱以极大的耐心论述了中国式线条在现代艺术中的意义:
它显然展示了马蒂斯强大的感受力,也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暂时将它称为书法式的。“书法式的”一词传达给我们的略有贬义之意。我们从来不像中国人或波斯人那样崇敬书法,我们立刻会想到那些老式的书写大师的浮华之名。但是,事实上,纯粹线条中存在着表现的可能性,而其韵律也许拥有各种不同的表现类型,以表现心境与情境的无限多样性。我们称任何这样的线条为书法,只要它所企求的品质是以一种绝对的确信来获得的。不过,这省略了这样获得的究竟是何种品质这一真正要点,是雅致而敏感的,还是粗野而自以为是的。因此,在称这种素描是书法式时,我并不是在指责它,因为事实是,马蒂斯线条的品质是如此超级敏感、如此细腻、如此不同于华丽的表演或炫耀,以至于,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它真的欺骗了无知之人,使其以为这只是无能而已。[12]
为了说明线条的品质,弗莱比较了两位画家的作品,其中一位是英国的西克特(Walter Sickert)。弗莱认为西克特的素描反映了日本书法的特征,即有自我意识,强调炫耀和表演(而中国书法艺术似乎一直强调无意识,强调“无意于佳乃佳”)。弗莱说:“通过比较的方法,我们可以回到沃尔特·西克特精致的素描中来,以便更清晰地弄清楚现代素描观的独特性,因为西克特的灵感并不是原创的,它可以追溯到惠斯勒(Whistler)。如今,通过惠斯勒,一种更富弹性、更为细腻的节奏已经从日本,遗憾不是从中国,被引入欧洲的素描艺术。”[13]
为什么是从日本而不是从中国引入书法,对欧洲艺术来说是一种令人感叹的遗憾?其实弗莱在我们刚才引用的这段文字中已经点明,根源就在于线条(极其宽泛地讲)可以有两种:“是雅致而敏感的,还是粗野而自以为是的”。在弗莱看来,日本的书法武断而充满自我意识,不像中国的书法那样细腻,也不像中国书法那样没有刻意炫耀的自我意识。
在下文中,弗莱通过谈论戈迪尔-布热津斯卡(Gaudier-Brzeska)的作品,继续了这一论点:“这里复制的后期戈迪尔-布热津斯卡的素描表明,要是他能活到今天,他或许会成为一个结构性制图家。这幅素描当然拥有一种紧张而又实用的线条,表明了想要达到那种最伟大的艺术的极其简练的陈述欲望。与此同时,人们也会说,它是这位极具天赋的雕塑家所留下的大量素描作品的例外,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素描不仅是书法式的,而且倾向于一种激情洋溢的、表演展示般的效果,令人想到日本人那种武断而又充满自我意识的书法。”[14]
至于雅致而敏感的线条,弗莱其实已经先行列举了两位更年轻的英国艺术家的例子:“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更年轻的艺术家,例如妮娜·汉姆内(Nina Hamnet)与爱德华·沃尔夫(Edward Wolfe)的素描的复制品,我们还能更清楚地看到同一种趋势。书法是新的类型,比旧有的更微妙、更细腻,也更自然,但最先震惊我们的还是其书法。确实,人们会惊讶地发现这么年轻的艺术家的素描,能以如此欢快的自由从自我意识中摆脱出来,完全避免了华丽的表演与炫耀。”[15]
至此,我们已经完全明白了,弗莱认为,最宽泛地说,他所比较的西方几位画家素描中的线条,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武断、炫耀、充满自我意识;另一类则是尽量避免过于强烈的自我意识,避免华丽的炫耀。尽管弗莱是一位对东方艺术有着了不起的、超一流感受力的艺术批评家,但是他将第一类书法与日本书法进行类比、第二类书法与中国书法进行类比,仍然表明了他对东方艺术的了解毕竟是隔靴搔痒。因为日本有雅意之极的书法,例如平安朝诸大师的作品,而中国也并不缺乏华丽、炫耀的书法,张旭、怀素的狂草显然就充满了强烈的自我意识与表演意识(所以米芾才会如此反感这些作品,认为它们脱离了晋人的雅致,以及“不期然而然”的自然之美)。
作为一个欧洲批评家,弗莱对东方书法的不同风格的辨别力,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地步。他感受力敏锐、细腻,能充分感知不同画家素描的不同质感,而这也得益于他长期的绘画训练(弗莱终其一生都没有放弃绘画)。当然,中国书法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名家辈出,灿若星空。而中国传统书法批评语言之丰富、感受力之精微,中国传统书法品评的词汇之富赡、色彩之华丽,足以让弗莱等人捉襟见肘,同时令西方艺术史家汗颜不已。例如,著名艺术史家巴克森德尔这样说:
我向来歆慕中国,尤其是歆慕她的书法传统。这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明显的原因便是:这个传统赋予了中国文化一种深刻的特质,我愿称之为一种介于人人都具备的言语与视觉文化之间的“中介语汇”(middle term)。甚至通过译文,我们西方艺术史家依然能够体会到中国的古典艺术批评缜密细腻,平稳连贯,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种“中介语汇”的存在。[16]
不奇怪的是,当巴克桑德尔面临缺少批评文献来描述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椴木雕刻的困难之际,他立刻会想到同时代的书写学校里那些书法教科书,而且从那些书写风格的描绘中借用词汇,以此作为“时代之眼”,来观看同一时期的德国雕塑。其立论之精致,方法之巧妙,惊采绝艳,令人羡慕。[17]
其实,远在现代认知心理学普及和当代神经科学的大量成果面世之前,像罗杰·弗莱那样伟大的艺术史家和批评家就已经直觉地感受到分析新艺术需要全新的方法,而他自己就是将这些方法系统地上升到一种美学高度的人。在晚年于剑桥所做的史莱德讲座里,弗莱重新探索了艺术家的感性这一话题,并概括了其主要思想:
首先,我们所说的感性是什么意思?它对我们有何意义?我们可以做一个最简单的试验,就是在一道借助直尺画出的直线与一条徒手线之间进行一下比较。直尺线纯粹是机械的,而且正如我们所说是无感性的。而任何徒手线必定会展现书写者的神经机制所独有的某种个性。这是由人手所画出并为大脑所指引的姿势的曲线,而这一曲线至少从理论上说可以向我们揭示:第一,艺术家神经控制能力的某种信息;第二,他的习惯性神经状况的某种东西;最后,在做出那个姿势的瞬间他的心智的某种状态。而直尺线除了两点之间最近距离这一机械的概念外,什么也不能表达……但是,如果我们像观看艺术品那样来观看一条徒手线,那么它就会告诉我们某种我们称之为艺术家的感性的东西。[18]

迈耶·夏皮罗(Meyer Schapiro)
夏皮罗无疑属于弗罗芒坦所代表的那个艺术史和艺术批评传统的继承者。他对这一传统的贡献,是将形式问题转化为风格问题。除了对风格问题与艺术家人格及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充分认知,还有熟练运用多种艺术史方法(包括形式主义、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和艺术社会史)取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史个案研究的成果外,夏皮罗的以下说法,可以被理解为他在风格问题上(一端是作品风格,另一端是社会)所持的一种艺术哲学:
因为绘画在当时已经不再再现人的理想类型,已经失去了与宗教和神话的古老联系,而艺术的价值[甚至是往昔艺术的价值]也都从手艺的微妙,及其对色彩的兴趣中得到评估,因此,在作品的感性材料中,对人性及其各种模态的这种充满狂喜的感知,成了一种重要的启示。它确保了隐蔽的个人世界深刻表现的可能性,否则,这种可能性往往被认为不过是炫技的手艺罢了。[19]
当艺术的价值被认为不再内在于题材和主题之中,而是内在于风格(手艺的微妙以及作品的感觉材料)之中时,艺术史和艺术批评某种意义上就发生了一次范式革命:这标志着古典艺术史和艺术批评的终结,以及现代艺术史和艺术批评的开端。而弗罗芒坦和夏皮罗,乃是我们一直在加以描绘的那个伟大的西方艺术史传统的代表。不难理解,为什么夏皮罗会完全认可弗罗芒坦的以下观点:
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他自己的对象上,他以一流专家的资质通晓自己的领域,在首次面对某些事物时,他发动了他的全部人格力量,以及对该领域的全部知识。他关于佛莱德斯和荷兰绘画所说的东西,有许多是以前的人们说过的,至少是笼统地说过的;但是,在弗罗芒坦的经验里有一种人们几乎从来不可能在其他作家那里发现的鲜活性和敏锐的胃口。[20]
也因为这个缘故,夏皮罗才能完全认可弗罗芒坦的判断,并提出了以下总结性的结论:
弗罗芒坦持久的批评性关注,集中在艺术作品的美学层面,正好提供了许多人认为丹纳所缺乏的东西。[21]
遗憾的是,在中文语境里,我们只有傅译丹纳《艺术哲学》——而且因为傅雷先生更为唯美的文字,使得这部本来就辞藻繁富的著作吸引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却没有弗罗芒坦的《比利时与荷兰的老大师们》。因此,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仍然处于西方古典美学和古典艺术史的氛围里。我常常想,理论的旅行与书的命运结伴而行。傅译丹纳《艺术哲学》滋育了好几代中国人,同时也贻害了数代中国人。它以华丽的语言和堂皇的大词,遮蔽了风格分析的根本亏欠。
夏皮罗所在的那个艺术史传统,得益于艺术史家拥有批评家一般的敏锐眼光和鉴赏判断的能力。与此互为表里的则是艺术史家的个人笔法或书写风格。我们不能说丹纳的个人笔法不好,在俘获艺术爱好者方面,他早已被证明是超一流的写作者。然而,正如我在前面反复提到的,一个稍微老练的读者是多么容易厌倦于膏腴其华、贫瘠其实的作风。在他关于荷兰画派的宏大叙事里,人们是多么疑惑于他怎么连一幅具体的画作都不做分析?而在他关于伦勃朗的滔滔辞费里,人们又会多么遗憾于他为何连伦勃朗的基本人格也不加刻画?
因此,是弗罗芒坦极大地推进了法国艺术史研究的进程。而出人意料的是,这样重大的贡献,却是一位小说家和画家做出的。除了画家对绘画专业知识的精通外,弗罗芒坦还是一位最擅长书写艺术家对作品的切身感受的作家。对此,夏皮罗有极为精确的观察和揭示。由于它的重要性和精彩性,兹不避冗长,援引于此:
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天赋,在他艺术批评的实质与风格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对他的批评方式来说非常关键的感觉与情感统一性,在他那个时代同样也是富有想象的写作原则,即通过一种敏锐的感受力来再现外部世界。在19世纪的小说和诗歌里,特别是在法国,个体的内在生活[不管是故事里的人物还是作家本人]成为主要的对象,并通过与弗罗芒坦用来描绘古代绘画的经验一样的精致画面来加以揭示。事实上,他是最早在艺术批评中引入法国小说家和诗人们发展出来的那种情感观察和表现标准的人:它要求直面对象,对情感的细腻表述,以及带有活泼句法、情感丰富语言的敏捷而又灵活的散文,能够将被观察者与观察者结合在一起,却不会在感觉或情绪中使对象全盘消解。“我以我笔,写我胸臆”乃是一种个人风格的理想。[22]
这一点难道不正是夏皮罗的追求吗?我总觉得,在欧美艺术史的伟人祠里,夏皮罗是独树一帜的。他的独特远不只是博闻强记、包罗万象的学问,不只是他那特立独行的思想者的风范,更在于他的写作风格。在这方面,潘诺夫斯基同样拥有经天纬地的知识,华丽的语言和思想天赋;贡布里希则是一位配备科学家大脑的思想者、滔滔雄辩者、妙极机神的写作者。夏皮罗似乎兼有潘氏的机敏和贡氏的思辨才能,但他更突出的却是足以与莫雷利、贝伦森和弗莱相提并论的细腻敏锐的图画感知能力,以及足以与弗罗芒坦媲美的写作才华。
面对潘诺夫斯基竭泽而渔的德国式研究,后人常常感到难于置喙;面对贡布里希滔滔雄辩的思辨力量和科学家一般的严密论证,读者时时觉得无从超越。与他们相比,夏皮罗似乎要谦虚低调得多,他的写作总是那么明晰而适度,他几乎没有写过一部大部头的书,却以其字字珠玑的小品赢得了一代又一代读者。他的写作短小精悍,是经验主义的和临时的;正因为如此,它们才确保了继续研究的可能性。在夏皮罗关于库尔贝和印象派研究的基础上,T. J. 克拉克完成了《人民的形象:库尔贝与1848年革命》和《现代生活的画像:马奈及其追随者艺术中的巴黎》等皇皇巨作,就是鲜明的证据。夏皮罗对新艺术史的压倒性影响,在T. J. 克拉克的鸿篇巨制《现代生活的画像:马奈及其追随者艺术中的巴黎》开篇中可见一斑:“此书的主题是印象派绘画与巴黎。就我的记忆所及,促使它诞生的源起是迈耶·夏皮罗1937年1月在一份名为《马克思主义者季刊》(The Marxist Quarterly)的短命杂志上首次发表的一些段落。夏皮罗写道,早期印象主义的力量,不仅仅在于涂绘的乐趣,或对阳光与色彩的单纯嗜好。马奈及其追随者们的艺术具有一种显然的‘道德面相’,这在他们那种将视觉真实的解释与社会自由的解释相结合的方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23] 或许,这既是夏皮罗学生众多、桃李满天下的原因,也是今天的哥伦比亚大学拥有两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教席的缘故。
注释
[1] Meyer Schapiro, Theory and Philosophy of Art: Style, Artist, and Society,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1994, pp.116-117.
[2]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上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24页。
[3]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上册,朱光潜译,第325—326页。
[4]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上册,朱光潜译,第327页。
[5]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上册,朱光潜译,第327页。
[6] Meyer Schapiro, Theory and Philosophy of Art: Style, Artist, and Society, p.113.
[7] 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25—226页。
[8] 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第229页。
[9] 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第3页。
[10] 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第7页。
[11] 罗杰·弗莱:《弗莱艺术批评文选》,沈语冰译,江苏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216页。
[12] 罗杰·弗莱:《弗莱艺术批评文选》,沈语冰译,第217—218页。
[13] 罗杰·弗莱:《弗莱艺术批评文选》,沈语冰译,第219页。
[14] 罗杰·弗莱:《弗莱艺术批评文选》,沈语冰译,第222页。
[15] 罗杰·弗莱:《弗莱艺术批评文选》,沈语冰译,第221—222页。
[16] 巴克森德尔:《意图的模式》,曹意强等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页。
[17] 参见麦克尔•巴克森德尔:《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椴木雕刻家》,殷树喜译,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
[18] Roger Fry, Last Lectures, Slade Professor ofFine Arts in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33-1934,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Kenneth Clark, Bently Hous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9, pp.22-23. 以上关于罗杰·弗莱的插曲,部分采用了我在《笔触的价值:弗莱论线条在现代艺术的地位》一文中的内容。
[19] Meyer Schapiro, Theory and Philosophy of Art: Style, Artist, and Society, p.105.
[20] Meyer Schapiro, Theory and Philosophy of Art: Style, Artist, and Society, p.112.
[21] Meyer Schapiro, Theory and Philosophy of Art: Style, Artist, and Society, p.116.
[22] Meyer Schapiro, Theory and Philosophy of Art: Style, Artist, and Society, pp.109-110.
[23] 参见T. J. 克拉克:《现代生活的画像:马奈及其追随者艺术中的巴黎》,沈语冰、诸葛沂译,徐建校,江苏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27页。
(注:沈语冰:复旦大学艺术哲学研究中心,本文节选自《图像与意义:英美现代艺术史论》商务印书馆 2017,经受权转载。)
关键字:黑格尔,弗莱,书法,绘画,线条,现代美学 艺术史内容标签: 黑格尔 弗莱 书法 绘画 线条 现代美学 艺术史

献给世界,你的真心,以致来世,以致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