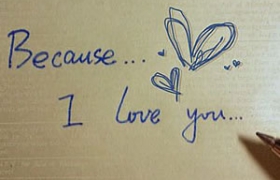美国当代画家吉姆·戴恩(Jim Dine,1935-)的艺术,旨在用象征的修辞语言来追求艺术生命。探讨戴恩的艺术语言,既可以帮助我们对二十世纪后半期西方前卫艺术的发展进行历史的再认识,也可以帮助我们展望下个世纪艺术的生存形态。 记得国内的一家美术杂志过去在介绍吉姆·戴恩时,称其为“波普大师”,而现在西方美术界又称他为“我们时代的伦勃朗”。我查了一下美国六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出版的美术史,发现这两顶桂冠都不是张冠李戴。尽管美术史上明白无误地写着,戴恩是波普群中最后一个被人们承认的大师,但是,他本人却从不认为他是波普艺术家。也许有人要说,戴恩的否认不过是艺术家们故作深沉的惯用技俩,然而,这却给了我们一个修辞的切入点,让我们有机会从这两顶桂冠的关系来看戴恩的艺术,并在当代西方艺术的大背景中见出戴恩艺术的历史意义。

所谓历史意义,指的是二次大战后,以美国新前卫为代表的西方先锋派美术同当今后现代美术的冲突与调和,及二者关系中可能暗含的下个世纪的艺术趋势。虽然在新世纪来临之时,后现代的“超级文本”有能力在技术方式方面宣告艺术的终结和文化的终结,可事实是,西方艺术界和学术界现在最热门的一个话题,是艺术的生存性(viability),即生存能力和生存形式,而不是生存的可能性。戴恩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经历的艺术道路,从“波普大师”到“我们时代的伦勃朗”,说明的正是艺术生存的能力及其各种形式,而不是形式的毁灭和能力的衰竭。戴恩之艺术的生存性,在相当程度上说,得自其修辞语言的使用。 戴恩生于1935年,他在1958年正式进入美国当代画坛。这个来自辛辛纳提的外地人,一进纽约就气势不凡,与比自己大四岁的同乡朋友、波普干将威斯尔曼(Tom Wesselmann)同开画展,然后又与另一个波普干将奥登伯格(Claes Oldenberg) 一 道搞起了环境艺术。作为波普艺术家,六十年代的戴恩身上充满了杜尚和达达的锐气,他那一群人的矛头,直指当时正走红的抽象表现主义。我们不会忘记,理希腾斯坦画过许多模仿印刷品点迹的卡通画,用来嘲弄抽象表现主义的笔触。当抽象表现主义宣称个人的精神世界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时候,理希腾斯坦却用瓦尔特·本杰明对机器复制时代的悲哀,来宣判个人主义文化的死亡。如果本杰明没有自杀,如果他能够长寿到二十世纪末来看当今数码复制时代的超级文本,那么他说不定会成为后现代社会的悲观主义者,会宣告人类精神文明的彻底死亡,或者象哈贝玛斯、詹姆逊那样,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来批判今天技术社会的悖人性。 戴恩并没有随大流去唱时代的挽歌,相反,他从自己所攻击的抽象表现主义艺术中,发现了表现的形式,正是这一形式将他从波普的虚无主义中拯救了出来。他没有沿着六、七十年代的波普道路而走向八、九十年代后现代主义的虚无之中。毫无疑问,后现代的价值在于其反中心主义的多元化倾向,但后现代的虚无,也恰恰出自这一倾向。戴恩没有追随激进的、反文化的虚无主义极端前卫,他通过抽象表现主义的笔触,回到了艺术的绘画性中。与美国六十年代抽象表现主义相近的主流艺术,是“后绘画抽象艺术”,戴恩借助抽象表现主义而追求的,是这之前的绘画性。 我第一次看戴恩的作品,是一九九三年看大型文献展“波普艺术”中戴恩创作于六十年代初的作品。那时,他将现成的装置,放在纯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的背景前,用三维的实物,来打破抽象绘画的平面性,又反过来用抽象绘画的笔触,赋予现成品以绘画性。例如,他将一具淋浴喷头安装在两幅上下对接、风格各异的纯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前,名之为《大淋浴一号》。照我的理解,平面抽象与现成装置的合一,是戴恩对调和与中庸的追求,是戴恩对当时具有反文化倾向的波普前卫和当时属于文化主流的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的调和,这完全不同于理希腾斯坦对抽象的嘲弄。可以说,这是戴恩对波普的狭隘和线性思维方式的超越,是他对波普的最初的不恭和背叛。

第二次看戴恩的作品,是一九九五年看他的专题素描展。大概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戴恩去东欧旅行,他在那里的博物馆和老式建筑中,看到了许多古代雕刻。在古典艺术面前,在前辈大师的形式语言的无比力量面前,他深深震惊了。整个东欧之行,戴恩都处于似幻似真的亢奋之中,直到返回美国才清醒过来,于是打算用素描写生的方式去复制那些雕刻作品。他向一家艺术基金会申请到一笔资助,到东欧的几个国家去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都象小学生学画石膏像一样,到博物馆去毕恭毕敬地画写生。戴恩画的雕刻非常写实,但里面又有很多主观的东西,它们是戴恩艺术力量的源泉。我们常说起绘画的力度,纯写实艺术的力度来自被描绘的对象的力度,画家的功夫在于怎样捕捉对象身上的艺术力量,即所谓再现的力量。但是,戴恩是表现性的,他这一时期的艺术力量,与他早期对抽象表现主义之笔触的钟情分不开,他的素描写生,是将对象的艺术力量,同化进自身之中,然后再外化到纸面上。这种力量,来自文艺复兴式的对古典意识的个性化追求。因此,他笔下的形非常写实,但这写实形像中蕴藏着的艺术精神,却是极其主观的表现。换句话说,戴恩把僵硬的、残破的石像,画成了有生命的造物,他把自己的血肉和灵魂之气,注入到了对象之中,使他的作品拥有了伦勃朗般的内在力量。这是八十年代的事情,当时风起云涌的后现代主义正时兴极端前卫的偶像破坏运动。在这反文化的大潮中,同性恋和爱滋病艺术打着“政治上正确”的旗号,向现代主义文化的“精英主义”发起了进攻。然而,精英主义本身也是后现代文化的一个方面,即社会批判性,它继承自现代主义的理想。在后现代关于人类文化和文明的这种矛盾态度中,戴恩摒弃了波普以来极端前卫的反文化倾向,他在古典艺术的人文主义精神氛围里,以对旧偶像的重新认识和对新偶像的人格创造,而享受了历史和文化的认同。 第三次看戴恩的作品,是一九九七年看他的九十年代中期近作展“新版本”。这些创作于九五、九六年的蚀刻版画作品,向我们展示了艺术家成熟的语言,即以意象为图像符号的象征语言。看戴恩的近作,最深的印象是,他有一整套业已建立的语言系统,这一系统的要害,是作为象征符号的意象。戴恩意象中最为我们国内艺术家熟悉的,可能是无处不在的心型符号,其次还有鸟、骷髅、浴袍等。 早在六十年代的波普作品中,心型意象就已经出现了,并且伴随了戴恩一生的创作。由于心的不断出现,它作为符号就具有了历史的重复性,并在不同的艺术时期具有不同的外形和内含。按照西方原型批评理论的说法,这种重复使意象超越了简单象征的层次,而揭示了一个蕴意深刻的原型。原型是艺术家的创作母题,也是艺术发生的心理和文化根源。 戴恩在波普时期画的心,有相当的抽象表现主义特徵,而且非常符号化,其象征性与西方瓦伦丁的传统有关。相传瓦伦丁是古罗马时期的一位祭司,他死后成为爱的保护神。在英语国家中,每年二月十四日的情人节,便称为瓦伦丁节。在戴恩早期的抽象表现主义笔触中,瓦伦丁的心有相当的浪漫色彩。后来这一意象之内含的变化,是浪漫色彩的减弱和观念色彩的加强。在一九九六年的《圣安妮》中,基督教的母题一目了然,但作品的主题却显然不再是基督教的浪漫故事。在犹太传说中,安妮是耶稣之母,虽然圣经中并没有关于圣安妮的事迹,但自中世纪以来,圣安妮便演化为生命和生育的守护神。于是在西方美术的传统中,她便总是与小女儿在一起,且以伴读的母亲为典型形像。戴恩的《圣安妮》采用了这一母题,但传统的形像荡然无存,我们看到的是两幅并列的安妮全身像,一是类似阳刻的蚀刻印刷,另一是黑白底片式的阴刻蚀印。在这一白一黑之间,戴恩用了一个悬浮的骷髅来打破阴阳之界,使两个世界得以沟通。在画面的下部,他画了一个大大的红心,漂游在整个蚀刻的表面。这颗心本身是基督献身救世的象征符号,同时也是生命的象征符号,它在隐喻的意义上与安妮的象征相吻合,但在绘画形式的意义上,它又以强烈的色彩、立体的造型和漂浮游离的位置,而与安妮的传说拉开了距离,并改变了整件作品的象征含义。

此一改变,也见于一九九五年的另一作品《技术色彩之二》的原型及其变形中。所谓变形,是指原型的各种显现形式,因为原型总是被不同的变形暗含着。这件作品是并置的侧面骷髅和乌鸦头像。前者是彩色的,后者是黑白的。这种色彩处理,颇为幽默,它让我们想起了戴恩的波普时期。骷髅的背景是纯抽象表现主义式的偏蓝的单色墨印,骷髅本身则几乎由三个原色构成。占三分之一面积的后脑骨为绿色,前额和面部呈黄色,处于画面正中的耳部是红色的心。我们知道,对现代电子技术来说,三原色是红、黄、绿,而非红、黄、蓝。若要细看,戴恩也用了间色来画骷髅,即眼窝阴影处的紫兰色和颚部的橙黄色。骷髅的牙齿几近纯白,与背景形成反差。此处大块面的色彩设置,明快简洁,以响亮和力度而给骷髅以生命。这小丑式的活生生的骷髅,既有波普的幽默,又有后现代的反讽。那象征生命的红色的心,处在这一切的正中,是对严肃的基督教象征意义的解构,是对传统的象征语言的颠覆。在一九九六年创作的《心血管》中,心之象征性的这一历史演化更加直观。 这一作品是两个红色的心在墨蓝色背景上的并置,左幅的心较为抽象化、形式化,让人联想到以往那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心的图形,右幅的心偏向写实,戴恩甚至画出了被切断的两根主动脉血管。也就是说,作者有意将自己的象征往生理方向引导,让象征从宗教走向现世,以便能够有可能从物质主义(恕我此处回避“唯物主义”一词以免混淆)的角度去反省现代艺术的理想主义。戴恩的这一方式,也是对后现代时期的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的解构。文化唯物主义,也称新历史主义,它用片段的眼光去横向地看待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环境,从而将作品从历史的发展大系中孤立出来。这当然与戴恩主张历史回归的艺术倾向不合,所以他才用并置的方式来求得对前卫的反讽。 在象征的意义上,戴恩作品中鸟的意象与心的意象异曲同工。让我们回头再谈《技术色彩之二》。与骷髅并置的乌鸦,是食腐动物,因而其象征便与骷髅的含义互补。二者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死亡的象征,而不同在于,骷髅是死亡的主体,乌鸦却是旁观者。戴恩的处理手法是逆转的,他用波普的色彩来赋予骷髅以生命,又用单色蚀印来否认食腐者的生命。在这逆转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哪个生命是真实的?戴恩在此所思考的生命,是艺术的生命。早在波普时期,当谈到艺术与生命之间的鸿沟时,戴恩就曾说过,隐喻和意象是座桥梁,它们的象征作用可以使艺术和生命获得同一。在戴恩画展的展厅里,有一部关于他艺术创作的录像资料片供人参考。戴恩在影片里说,他的艺术观念是关于艺术本身的观念,他对后现代时期那些时髦的政治话题没有什么兴趣。因此,对戴恩来说,唯有艺术的生命才是永恒的生命。 有了这种生命观,《技术色彩之二》中骷髅意象的象征意义就好解释了。按照西方的文化传统,头脑是人的精神殿堂。这座神殿的幽深与复杂,正如宇宙的幽深与复杂。一个人是一个宇宙,人类的艺术,也以其深刻、丰富和神秘而成为一个宇宙。宇宙、人、艺术的关系,在象征的意义上是等同的,同时也是创造和被创造的关系。骷髅与生命的相互转换,既是宇宙的永恒,也是生命的永恒,更是艺术的永恒。骷髅的复活,是后现代时期的文艺复兴,是我们人类在新世纪来临之时用自己的双手重新建造的希腊神庙。有了这个神庙的宏伟建筑,历代的雕刻便有了栖身之所,当代艺术也就有了自己的守护神。

在西方当代美术史的意义上说,抽象表现主义是五、六十年代的新前卫,波普是六、七十年代针对新前卫的新前卫,后现代主义是八、九十年代从波普演化而来的新前卫。戴恩总是在回顾过去,这是后现代主义中的一大倾向,正是对往昔的回顾,才使戴恩对艺术语言的探讨得以进行。然而,戴恩的回顾,是不是前卫艺术在世纪转折之时面对历史的忏悔?他对古老的象征语言的改造、他对旧语言的挪用、戏拟和并置,是不是对后现代中反文化潮流所鼓吹的艺术之死亡的逃避?戴恩用波普方式来赋予骷髅以生命,是不是象征了生命本身的永恒往复?戴恩的艺术被认为是关于艺术的艺术,那么他的不断回顾,是不是新世纪艺术生存的节奏和形式?他那心的原型,是不是暗示了艺术的不朽和生命的不灭? 戴恩的近作告诉我们,后现代主义并没有创造出一套新的艺术语言,后现代艺术所惯用的戏拟、并置、反讽之类,是自古希腊就有的修辞方式。后现代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后者一意破坏传统的语言,而前者则力图重新组织和利用旧的语言。九十年代反文化的极端前卫倾向之所以宣称艺术的终结,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偶像破坏行为中,似乎看到了语言的穷尽。可是语言是没有穷尽的,语言的无穷并不在于新语言的创造,而在于旧语言的翻新。由于极端前卫的偶像破坏已将前卫本身推入了自我否定的怪圈之中,偶像破坏运动唯有破坏自身而再无现成的其它目标,因此我相信,新世纪的艺术存在,仍会是对旧语言的重新组合和利用,包括对极端前卫的偶像破坏运动的重新利用。如果情形不是这样,我们就不得不给二十一世纪的艺术另下一个定义。

吉姆·戴恩


吉姆·戴恩作画


吉姆·戴恩作画后撕开作品
关键字:前卫,表现主义,抽象,骷髅,生命,象征,内容标签: 前卫 表现主义 抽象 骷髅 生命 象征

献给世界,你的真心,以致来世,以致未来